大脑中的“指挥官”
Robert Sapolsky
像大多数科学家一样,我也时常出席各种专业会议,神经科学协会的年会就是其中之一,该协会是全球大多数大脑研究者参加的一个组织。参加这类年会的经历所产生的思想启迪是你无法想象的。大约有2.8万名像我这样的科学界书呆子拥挤在一个会议中心。过不了多久,这种聚会就会让你感到可笑:整整一个星期,无论是下馆子、乘电梯还是进洗手间,你身边的人都会和你讨论有关鱿鱼的神经轴突问题。科学本身的发现过程更是不易。这场会议有1.4万个演讲和大量的宣传海报,信息量绝对让你目瞪口呆。对于那些你认为重要的宣传海报,你本打算进去听听讲座,却可能因为厅堂爆满而无法入内;或者演讲者的语言你一窍不通;或者其他非听不可的报告在论述你未来5年内计划进行的每一个实验步骤。全球的科学家似乎达成了共识:尽管这么多人在这个大脑研究的课题上不懈努力,但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仍知之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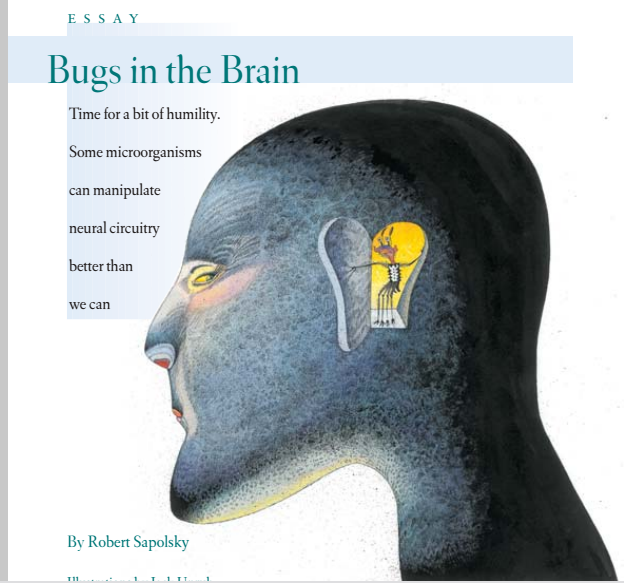
我对这次会议的情绪低潮终于在一天下午出现了。当时我正坐在会议中心的台阶上,被眼花缭乱的信息和自己的孤陋寡闻弄得晕头转向,我盯着路边一个污浊阴暗的水坑发呆,心里想,那个污水坑里的一些微生物对大脑的了解程度大概都比我们所有的神经学家知道的多。
我可能是最近看了一篇关于某些寄生虫如何控制其宿主大脑的文章后,才萌生了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一些教科书中所用的例子包含了体外寄生物,即那种寄生于人体表面的生物体。例如,某些Antennophorus类的螨虫趴在蚂蚁的背上,当触动蚂蚁的嘴时,就能够引起蚂蚁吐出吞下的食物,以供螨虫食用。一种Syphacia类的蛲虫可将它们的卵排在啮齿动物的皮肤上,这些卵进而分泌一种致痒的物质,当啮齿动物用牙齿搔痒时,卵就被吞入体内,蛲虫的卵一旦进入啮齿动物体内,就如鱼得水,孵化出幼虫了。
寄生虫通过骚扰宿主,使其行为方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生改变。但有些寄生虫实际上也改变了自身神经系统的功能,有时这种改变是通过利用影响神经系统的激素间接发生的。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一种甲壳类藤壶(Sacculina granifera),附着在雄性沙蟹身上,能分泌一种导致沙蟹母性行为的雌性激素。然后这种奇怪的雄性沙蟹同雌性沙蟹一起游出大海,在沙滩上挖坑产卵。当然,雄性蟹不能产卵,但是寄生虫——藤壶却能。如果藤壶侵入雌蟹体内,在使雌蟹的卵巢萎缩后(称为“寄生去势”),就能导致雌蟹产生与雄蟹相同的行为。
![1505681347447446.png @W9]W9JP5O3{(S0T4VFY3]3.png](http://www.hudongkepu.com/resources/image/20170918/1505681347447446.png)

虽然这些例子稀奇古怪,但至少这些寄生虫还呆在大脑之外。然而,有些寄生虫却想方设法进入宿主的大脑中。它们大多数是病毒性微生物,而不是像螨虫、蛲虫和藤壶等相对庞大的寄生虫。如果一只这样的小寄生虫进入大脑内,它基本上能够避开免疫系统的攻击,并且可以改变宿主的神经系统结构,使其为它们服务。
狂犬病毒就是这种寄生虫。虽然大家对这种病毒作用的了解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像我这样把它们与神经生物学联系起来。狂犬病毒在宿主之间的转移方式有许多种,它根本不用自己移到大脑附近。它可以设计一种窍门,如使用导致感冒鼻塞(即刺激鼻通道的末梢神经)的介质,使宿主打喷嚏而将病毒播散给别人,如剧场内前后排的人。或者该病毒能够诱发一种贪得无厌的欲望去舔舐人或动物,由此将唾液中的病毒传递出去。但是我们都知道,狂犬病毒能导致宿主的行为具有攻击性,因此病毒能通过进入伤口的唾液而传入另一个宿主体内。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情况。许多神经生物学家研究攻击行为的神经基础,包括相关的大脑路径、相关的神经传递介质、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激素的调节等。攻击行为的研究导致各种学术会议、博士论文、小规模的学术争论,令人不快的教职争夺战以及专著的涌现。但是,从一开始狂犬病毒就“知道”要感染哪些神经元,使受害者得狂犬病。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位神经学家为了了解攻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而专门去研究狂犬病毒。
不论这些病毒的影响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它们仍然有改进的空间。这是因为寄生生物具有非特异特征。如果你是一个患狂犬病的动物,你可能会咬狂犬病毒不容易复制的动物,如兔子。因此,虽然使大脑受感染的行为效应令人眩晕,但如果寄生生物的影响范围太广,它可能会碰上一个死对头。
到底是什么把我们带入一个关于大脑控制的美妙而特殊的案例,以及我前边所提到的由牛津大学的Manuel Berdoy等人发表的那篇文章上来呢?Manuel Berdoy和助手研究了一种称为模型体系弓行体(Toxoplasma gondii)的寄生虫。在弓行体王国中,寄生虫的生活包含了由啮齿动物和猫组成的所谓双宿主序列。原生动物被啮齿动物摄取,进而在其体内尤其是脑部形成胞囊。当啮齿动物被猫吃掉后,弓行体寄生虫便在猫体内再生。猫将这些寄生虫从粪便中排出,这些寄生虫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环节又被啮齿动物吞入。整个过程的关键在于其具备的特异性:猫是弓行体寄生虫能够在其体内进行有性繁殖并被排泄的唯一物种。因此,弓行体寄生虫不希望其载体——啮齿动物被老鹰叼走,或猫的粪便被甲壳虫吞掉。需要注意的是,弓行体寄生虫能感染各种类型的生物;但如果想传播给一种新的宿主,它还是要先在猫身上寄生才行。
正是由于这种寄生虫会感染到其他物种,因此所有“妊娠期指南”之类的书都建议孕妇不要把猫和猫食放在房间内,并警告孕妇避免在有猫出没的花园从事园艺劳动。如果猫粪便中的弓形体感染了孕妇,它就可能影响胎儿并有可能导致胎儿神经系统的损害。了解了这种情况的孕妇都离猫远远地,然而,受弓行体寄生虫感染的啮齿动物的行为则恰恰相反。这种寄生虫最拿手的把戏就是让锯齿动物的胆子变大了。
所有正常的啮齿动物见了猫都是躲闪不及,生态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固定行为模式”,因为啮齿动物不会因为反复试验而形成对猫的厌恶(因为啮齿动物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机会从猫爪子底下吸取错误的教训),因而它们对猫的恐惧是天生的。它是通过能够辨别信息激素(即动物释放的化学气味信号)的嗅觉来判断。即使在一生当中从未见过猫,这些数百代实验小鼠的子孙,也会本能地避开猫的气味,但除了那些被弓行体感染的啮齿动物以外。
这不是一般的寄生虫破坏中间宿主大脑,导致其注意力分散、不堪一击的例子。啮齿动物的其它方面看起来都是完好无损的。动物的社会地位在它们的优势等级中不会改变。它仍然对交配感兴趣,实际上也就是对异性信息激素感兴趣。受感染的啮齿动物仍然能够识别其他气味,只不过它们不会轻易地在猫散发的信息激素下退缩。这真是让人吃惊!这就好像某人的大脑感染了寄生虫,却不会对他的思想、情绪、SAT得分或电视喜好有任何影响,但是为了完成寄生虫的生命周期,他自身却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强迫自己去动物园,攀越栅栏对丑陋的北极熊来一个法国式的接吻。正如Berdoy小组在其文章标题中所提到的:这是寄生虫引导的致命吸引力。
很明显,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这样说不仅仅因为,任何科学文章在这一点上都是义不容辞的,而且是这个发现在本质上是如此的棒,人们一定要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还有,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古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时代,那个时代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进化是惊人的。其惊人之处在于它是违反直觉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毫不怀疑的认为,进化是定向的和渐进的:非脊椎动物比脊椎动物更加原始;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中进化程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是创世纪以来最奇特的哺乳动物等等。不管我在讲课中怎么强调这个观点的错误性,但我的一些最好的学生却始终喜欢这个论点。如果你对此观点深信不疑,那么你就不仅仅是错了,你也离人类方向性进化这一哲学不远了,这种哲学认为进化程度最高的是尝过炸肉排和会正步走的北欧人。
因此请记住,外界存在着能够控制大脑的生物。微生物甚至更大些的生物体比人类(当然也包括神经学家)有更大的力量。我在路边水坑的思考使我得出了一个与水仙在水中的倒影相反的结论。我们需要在物种演化史上保持谦虚的态度。我们既不是进化程度最高的种属,也不是刀枪不入的动物,当然,我们也不是最聪明的一类。
【王伟/译 赵辉/校】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