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1938年发现核裂变的参与者之一,梅特纳当年被诺贝尔奖评审人员所忽视了。种族迫害、恐惧心理和机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埋没了她的重大贡献。
当科学家在1938年末首次认识到一粒中子能使一个原子的核分裂时,这一发现完全出乎意料。事实上,从未有物理理论预言过核裂变,它的发现者一点也没有预见到它最终会用于原子弹和核电站。这一史实是无可争辩的。
然而,究竟是谁有资格享有发现核裂变的美誉,却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物理学家丽赛·梅特纳(Lise Meitner)和两位化学家Otto Hahn和Fritz Strassmann经过长达四年的研究,终于在柏林的实验室中发现了核裂变。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梅特纳逃离了纳粹德国,此后不久,Hahn和Strassmann报道了这一发现。几周以后,梅特纳和她的姬儿Otto R.Frisch发表了对核裂变的正确的理论解释。但是,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只授予了Hahn一人。
Strassmann没有与Hahn共享诺贝尔化学奖也许是因为他在研究小组中资历较浅,而诺贝尔委员会往往偏向年长的科学家。但是梅特纳和Hahn具有相同的专业资格。为何她被排除在外?Hahn的说法后来成了标准的理由,这种理由多年来被不加批评地采纳了。据他说,这一发现完全是依靠化学实验所得到的,而这些化学实验是在梅特纳离开柏林后做的。他坚持认为,也许除了延误了发现之外,梅特纳和物理学与他的成就毫不相干。

Strassmann与Hahn很接近,他却不赞同Hahn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梅特纳是他们智慧的领头人,即使在她离开柏林以后,她仍然通过与Hahn之间的书信往来,继续成为他们那个研究小组的一员。现在能够收集到的文件支持Strassmann的观点。科学出版物显示,导致核裂变发现的研究工作是多学科充分交叉的。对核物理的一些疑问开启了这一研究。从化学和物理学取得的数据和作出的假定引导着他们的进展,有时也误导了他们的研究。私人文件显示,梅特纳所作出的根本性贡献一直持续到该发现的完成之时。
无论从确定科学成就归属的哪一项常规标准来看,诺贝尔委员会也应该承认她的作用。但是在德国,当时的条件完全不正常。该国的反犹太人政策迫使梅特纳移居国外,把她与她的实验室隔离,禁止她作为共同作者报告裂变结果。迫于政治压力和恐惧,Hahn在该项发现作出之后不久就把自己和核裂变与梅特纳和物理学拉开了距离。随着时间的进展,诺贝尔奖把这些不公正的做法封进了科学史的尘埃。最近所公布的文件表明,诺贝尔委员会监没有弄清,这一研究成果既有赖于物理学又有赖于化学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也没有认识到,Hahn不是出于科学的原因把自己与梅特纳拉开了距离,而是因为政治压力、恐惧心理和机会主义。
其他一些因素对于排斥梅特纳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她在瑞典作为难民的局外人地位,战后在德国存在着不愿面对纳粹罪行的情绪,以及通常认为女科学家不重要,处于从属地位和常犯错误的观念(在当时这种观念比现在要强烈得多)。在当时,梅特纳很少公开说什么。私底下,她指出Hahn的行为“完全隐瞒了过去的真相”,即他们曾经是最密切的同事和朋友。她想必相信,历史终将站在她一边。五十年以后,历史确实站到了她一边。

研究铀
丽赛·梅特纳生于维也纳,并在那里受教育。她于1907年28岁时移居柏林。在柏林,她与同龄的化学家Otto Hahn合作研究放射性。在放射过程中,一种原子核通过发射α粒子或β粒子转变成另一种原子核。他们的合作因1918年发现了钋而扬名。钋是一种特别重的放射性元素。随着他们事业的进展,他们在科学水平上和专业职务上韭驾齐驱:他们都成为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的教授,每人都在该研究所里负责一个独立的部门,Hahn负责放射化学部,梅特纳负责物理学部。
在二十年代期间,Hahn继续开发研究放射化学技术,而梅特纳则进如了核物理学这个新领域。Hahn后来把这一时期称为她的研究使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获得了国际声誉的时期,而且在这方面梅特纳超过了Hahn自己。她的杰出成就以及她的奥地利国籍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时掩护了她。与其他大多数犹太人出身者不同,她没有被开除职务。虽然她的许多学生和助手是纳粹狂热份子,梅特纳还是觉得物理学太激动人心了,难以弃之而去。她特别对恩里柯·费米(Enrico Fermi)及其合作者在罗马所做的实验感兴趣,他们开始利用中子去轰击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
费米观测到,当发生中子反应时,作为靶的原子核并未发生剧烈变化:入射的中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引起作为靶的原子核只不过发射出一个质子或一个α粒子。他发现,重元素更容易捕获中子。也就是说,一个重的原子核会得到一个额外的中子,如果这一变得更重的原子核是放射性的,它就必然会发射出射线而衰变,衰变把这个原子核转变成下一个更高的元素。当费米用中子辐照已知最重的元素——铀时,他观测到有几种新的发射物,没有一个具有铀或铀附近元素的化学性质。于是,他小心地提出,他合成了铀以后的新元素。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为之入迷了。

梅特纳已经把费米的结果验证到这一点。这项研究完全适合她的志趣和专长,而且她正处于全盛时期:作为首批进入德国科学高层的妇女之一,她是她那个时代核物理学的一个学术带头人。然而,为了详细深入地研究这些新的“超铀元素”,梅特纳需要一位杰出的放射化学家。Hahn尽管一开始不愿意,后来还是答应给予帮助,该研究所的一位分析化学家Fritz Strassmann也参加了他们的合作。这三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一致的:梅特纳是“非雅利安人”,Hahn是反纳粹的,Strassmann因为拒绝参加具有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化学协会而在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之外难以谋生。
到1934年底,该研究小组报道,费米所观测到的发射物不可能归属于任何已知的其他元素,它们的行为方式属于超铀元素:它们可以与诸如硫化铂和硫化铼等过渡金属(硫化物)一起从反应混合物中分离出来。于是,这些柏林科学家也象费米一样,把这些活性物质初步定为铀以后的新元素。而事实是,这种解释韭不正确:它有赖于两个假设(一个出自物理学,一个出自化学),只经过几年时间就证明它们是错误的。
从物理学来说,直到那时一直只能在核反应中观测到发生很小的变化,使得象裂变那样的事件难以想象。从化学上来说,似乎超铀元素属于过渡元素。它是一个简单的错误:钍和铀的化学性质与过渡元素的化学性质极为相似,因此三十年代的化学家也预期铀以后的元素应该象过渡元素那样,与铼、锇、铱、铂相似。
解开衰变链
这两个假设互相支持,误导了这一研究达数年之久。后来,Hahn抱怨物理学家以及他们关于小的核变化的错误认识妨碍了核裂变的发现。然而,如果妨碍了的话,科学出版物表明,化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自满的,而物理学家则更持怀疑态度。物理学确实并没有预言裂变,但它探测到了化学所不能探测到的异常现象。

这些柏林的科学家试图从具有极强的天然放射性的铀和它的衰变产物中分离出设想之中具有极为微弱活性的超铀元素。在用中子对铀样品进行辐照之后,他们把样品溶解,然后只从溶液中分离那些具有过渡金属化学性质的活性物质,通常是利用过渡金属化合物作为载体。沉淀本身是几种发射物的混合物,柏林研究小组为此开始了艰难的清理工作。
在两年时间中,他们鉴定出两条平行的衰变链,他们将这两条链称为过程1和过程2[见框图]。这些衰变的顺序对应于铀以后元素预期的性质:它们类似于过渡元素铼、锇。等等。这些顺序和预期的化学性质之间似乎配合得太好了,不象是真的。以Hahn为主要撰稿人,1936年和1937年该研究小组欢欣鼓舞地在《化学报道》杂志上反复地把这些超铀元素称为“毫无疑问的”,它们的存在是“无疑的”,“不必进一步商讨”。
与此同时,这些资料数据正在使物理理论越来越难以应付。梅特纳奋力从化学、放射化学和她自己的物理测量来把实验结果解释成一种涉及核过程的有说服力的模式。她提出,热中子(极其缓慢的)提高了过程1和过程2的产量,证明这些过程中涉及到中子的捕获。但是快中子也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她的结论是,这两个过程都源自最丰富的铀同位素——铀238。她还鉴定出第三种过程(该过程涉及到捕获较慢的中子),这种过程中不存在链。
梅特纳觉得很奇怪的是,三种不同的中子捕获过程都起源自同样的铀238同位素。她怀疑,过程1和过程2一定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从理论上考虑,她不能理解捕获单独一个中子怎么能产生如此大的不稳定性,从而需要4次或5次发射才能消除这种不稳定性。而且更难理解的是,这两条长长的衰变链在几步发射中都相互平行。理论上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在1937年给《物理报》的一份报告中,梅特纳的结论是,实验结果“难以与当前的原子核结构概念相一致。
一旦认识了裂变后,研究人员就懂得了过程1和过程2是裂变过程:铀分裂成两个高度放射性的碎块,形成了一长串衰变。(由于铀能够以许多方式分裂,因此可以有许多这种衰变链。)梅特纳认为过程3是最正规的,后来证明这是正确的:在这一捕获中子的反应中形成的铀239同位素通过发射衰变成第93号元素。1940年,Edwin McMillan和Philip Abelson~定了这一元素,后来该元素被命名为镎(Np)。假如这些柏林的科学家当时能探测到镎,他们本应发现它是种稀土元素,他们还应认识到,过程1和过程2中的活性物质监不是超铀元素。但他们没有探测到镎,因为他们的中子源太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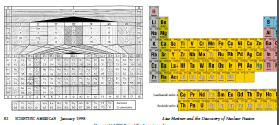
鉴定钡
柏林研究小组所犯的最严重错误是,他们只分离和研究了那些具有过渡金属化学性质的活性物质,而忽视了所有其他成分。1938年,伊伦·居里循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一居里的妻子,1935年与丈夫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和PavelSavi.tch在巴黎利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检验了铀产物混合物的全部成分,发现了一种新的强放射性物质,它的化学性质难以确定。就象假设中的超铀元素,它的产率因热中子而提高。但是,到1938年10月柏林研究小组开始研究它的时候,梅特纳却逃离德国,去了斯德哥尔摩。Hahn和Strassmann自已分析了居里的活性物质,发现它紧跟着一种钡载体,监鉴定它是镭的一种同位索。
梅特纳和Hahn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斯德哥尔摩与柏林之间的邮件隔夜就到。她几乎不能相信镭这一结果。如果要形成镭,铀核就应该发射2个α粒子。梅特纳坚信,一个中子在能量上不可能击出甚至一个α粒子,当然不要说2个了。1938年11月,梅特纳访问了尼尔斯.玻尔在哥本哈根的理论物理研究所。11月13日,Hahn在那里与梅特纳见了面。他俩在城外秘密见面,以避免给Hahn带来政治麻烦,Hahn以后也从未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但是,我们从Hahn自已的袖珍日记本中了解到他们见了面,而且我们知道梅特纳使劲地反对镭这一结果。这是Hahn带回给柏林的Strassmann的信息。
据Strassmann所说,Hahn告诉他,梅特纳“急切地恳求”他们再一次验证镭。Strassmaan回忆道,“幸运的是,她的见解和判断对我们来说非同小可,于是我们立即开始作必需的对照实验。”利用这些实验,他们旨在经过从钡载体上部分地分离出镭而证实镭的存在。但是分离不出镭来,他们被迫作出结论:他们的“镭”实际上是钡的一种同位素,钡是一种比铀轻得多的元素。
1938年12月,就在圣诞节前不久,Hahn告诉梅特纳有关钡的情况。他写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我们知道铀事实上不可能破碎成钡!”他希望她能提出”一些奇怪的解释。”梅特纳在信中对此作了回答。尽管她觉得难以想象一种“彻底的分裂”,她还是要他相信,“人们不能无条件地说:它是不可能的。”她的回信肯定是Hahn所收到过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她已经激烈地拒绝了镭这一结果,但她准备把钡这一结果考虑为对现有理论的一种拓展,而不是矛盾。
后来,人们知道Hahn说了假如梅特纳仍然还在柏林,她很有可能说服他不相信钡这一结果,很有可能“禁止”他作出这一发现。但是,Hahn一直握着的梅特纳的信证明,事实正好相反。而且在当时,Hahn清楚地发现,她的来信让人信心十足,因为只是在他收到此信后,他才在他关于钡的著作校对清样中添加了一段,指出铀核分裂成了两块。梅特纳对于她未能分享她所称的这一“美丽的发现”深感失望,但是他们都明白,在出版物中是不可能包括一个“非雅利安人”的。
修正核理论
梅特纳在圣诞节拜访了在瑞典西部的一位朋友,她的姬儿、玻尔的研究所里的物理学家Otto Frisch与她同行。当梅特纳与Frisch走在一起时,核理论的不同部分也交汇了。两人都习惯于把原子核看成一个液滴,但是现在他们都把它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振荡液滴,它很容易分裂成两滴。Frisch认识到,象铀这样大的一个原子核其表面张力可能极小。梅特纳在头脑中对质量亏损进行了计算,估计出原子核分裂时因转变成巨大的能量而损失的质量有多少。一切都已具备:理论解释本身是一个美丽的发现,而且人们也承认它是一个美丽的发现。物理学界立即接受了梅特纳和Frisch所提议的“裂变”这一术语,而且玻尔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用作探索一个更深人的理论的起点。

Hahn和Strassmann关于钡的发现刊登于1939年1月的《自然杂志》(Naturwissenschaf)。几个星期之后,梅特纳和Frisch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他们的解释。表面上看,裂变的发现现在完全是隔裂开来的,化学与物理学各自为政,实验与理论互不相干,德国人与难民各干各的。对于那些不懂科学或那些不想去理解政治问题的人,似乎是化学家发现了裂变,而物理学家只不过对它进行了解释。
在发现裂变后的几个星期中,Hahn利用了那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隔裂状况。他知道梅特纳被迫移民是不公正的。他知道她完全参与了这一发现。但他不能这样说。他为自己担心,也为自已的地位担心,他极其害怕别人会发现他和Strassmann在梅特纳逃离柏林后还继续在与她合作。他决定,裂变的发现只包括他与Strassmann在1938年12月所做的那些化学实验。1939年2月,他写信给梅特纳:“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物理学,相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进行着化学分离工作。”他把裂变说成是一件“来自天堂的礼物”,一项能够保佑他和他的研究所的奇迹。
后来的情况表明,Hahn原本没有必要把自已与梅特纳和物理学隔裂开来,以求得“奇迹成真。那一年春天,德国军方对于新发现的核裂变现象所具有的潜在用途大感兴趣,到了1939年夏天,Hahn和他的研究所都受到了保护。后来他回忆道:“裂变挽救了整个形势。”
在原子弹生产出来之后,裂变比以往更加容易引起轰动,Hahn成了一个十分著名的人物。在战后德国,他是整整一代人中的主要公众偶象,被捧为诺贝尔桂冠得主,一位从未向纳粹屈服的正直的德国人,一位没有制造过原子弹的科学家。然而,他对梅特纳的所作所为却一点也不正直。在他数不清的著作、谈话、回忆录或自传中,他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梅特纳对铀研究项目的开创性贡献,也没有提到她对柏林研究小组的领导作用或她离开后他们的合作。1968年,他在哥廷根去世,享年89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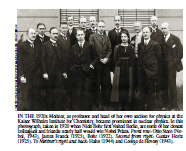
在战争年代,梅特纳在瑞典的专业地位很低。她的朋友们相信,假如她移民到其他任何地方,她几乎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的。1943年,她接到邀请,请她到洛斯阿拉莫斯去从事原子弹的研制,但她拒绝了。战后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她在美国和英国很出名,被人不适当地称为带着原子弹的秘密逃出纳粹魔掌的犹太难民。但是,梅特纳是一个厌恶张扬喜欢宁静的人。她从来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授权别人为她写过传记。1960年,她离开斯得哥尔摩去了英国剑桥,1968年在她90岁生日前几天在剑桥与世长逝。令人痛心的是,直到她去世近30年之后,她的研究工作才得到合理的承认。
图l梅特纳被认为是她那个时代的最杰出的核物理学家之一.尽管她在整个成年生活中一直抽烟并从事放射性研究,她却一直活到了9O岁.右图为Otto Hahn和梅特纳在1910年左右在柏林大学他们的实验室中所拍摄的照片.他们从l9o7年起到1938梅特纳被迫逃离纳粹德国为止,一直是同事和好朋友。

图2梅特纳的物理仪器从1934年到1938年一直被柏林研究小组用于最终导致发现核裂变的研究。从五十年代起,这些仪器就以“Otto Hahn的工作台的名义在德意志博物馆中陈列了大约30年之久,只有在一条附带的说明中提到了Fritz Strassmann,却根本没有提到梅特纳。
图3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元素周期表(左)引导研究人员期望铀以后的元素会是过渡元素.在四十年代发现了几种超铀元素以后,Glenn T. Seaborg认识到铜系元素构成了类似调系元素的第二类稀土元素系列(右边为1995年的元素周期表)。1994年,第109号元素被命名为meitnerium以纪念梅特纳.
图4在二十年代,作为凯撒·威廉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和她自己所在的物理学部的负责人,梅特纳已经在核物理学占有杰出地位。此照片是在1920年尼尔斯.玻尔初次访问柏林时所摄,照片中有一些她的最密切的同事和朋友,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前排为OttoStern(1943年诺贝尔奖得主),James Frank(1925年诺贝尔奖得主)、玻尔(1922诺贝尔奖得主)。后排右边为古斯塔夫.赫(1925年诺贝尔奖得主)。梅特纳右边和背后为Hahn(1944年诺贝尔奖得主)和GeorgedeHevesy(1943诺贝尔奖得主)。

图5 Otto R.Frisch与梅特纳在1939年首先解释了裂变过程。他于1940年在英国与流亡英国的同胞Rudolf Periels一起分析了将核裂变用于武器的可能性,并帮开创了盟国的原子弹项目。
图6在导致发现核裂变的研究中,Fritz Strassmann与梅特纳和Habn并肩工作.他的分析化学知识对于鉴定钡是十分关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个勇敢的反对纳粹主义者.他还曾帮助拯救了一个犹太人朋友的生命。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