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测序离临床有多远
一些罕见病例已经因为基因组测序技术而受益,但这项技术能否在临床领域普及,却还面临很多难题。
撰文 布雷登·马赫(Bredan Maher) 翻译 赵瑾
女儿刚生下来,黛比·约尔德(Debbie Jorde)就注意到,女儿的双臂以极不自然的角度弯曲着。不仅如此,她的女儿还有其他问题:腭裂、手指和脚趾都只有八根,而且没有下眼睑。医生确诊黛比的女儿患有米勒综合征(Miller syndrome)。这种疾病非常罕见,以至于医生长期把这些病例归咎于自发性突变(spontaneous mutation),而非家族遗传。因此,医生当时告诉黛比,如果生第二胎,孩子患此病的几率不会超过百万分之一。
不幸的是,医生错了。三年后,黛比生了一个儿子,出现了同样的病征。黛比的现任丈夫 —— 林恩·约尔德(Lynn Jorde)是美国犹他大学的遗传学家。当黛比重述医生当时的话时,林恩现在仍会心里发毛。“在当时的情况下,医生给患儿家属的正确回答应该是:这种病例十分罕见,所以我们无法预测你下一个孩子的患病风险” 。

由于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出现,黛比和她的孩子现在知道了他们家族所面临的遗传风险。林恩与合作者一直想对受到遗传疾病困扰的家庭进行基因组测序,寻找疾病相关突变,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研究致病基因的遗传模式,而她的妻子成了理想的研究对象。黛比和前任丈夫以及她的两个现已成年的子女 —— 希瑟(Heather)和罗根·马德森(Logan Madsen),都很乐意参加这项研究。2009年,他们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接受全基因组测序的家庭。
6个月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对4个人的基因组数据作了交叉比较,后来又对比了其他米勒综合征患者的基因组序列,最终确定了与此病相关的基因 —— DHODH。这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会参与核苷酸的合成。研究发现,这种疾病其实是隐性遗传的。在黛比的例子中,她和前夫都携带了一个DHODH基因突变体,因此他们的孩子患这种疾病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这项研究还发现,黛比的两个孩子还携带着一种基因突变,会导致影响肺部发育的隐性遗传疾病 —— 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黛比说:“在此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得肺炎。”
像黛比这样的家庭虽然很少,但数量在不断增多,而这些家庭的大多数成员都患有罕见的疾病和癌症。目前,科学家已对这类人群中的不少人进行了基因组测序,以便于诊断或研究病情。对于希瑟和罗根来说,虽然基因组测序对疾病治疗没什么帮助,但在测定其他一些病人的基因组序列时,却是带着这个目的进行的。去年,根据基因组测序结果,医生为一位美国男孩做了一次风险很高,但能救命的骨髓移植手术;另一名患白血病的妇女在基因组测序后,决定不采用高风险的手术疗法;医生在治疗一对患有罕见疾病的双胞胎时,也曾根据基因组测序改进治疗方法(见“从60亿到1”)。
迄今为止, 在接受过基因组测序的遗传病患者中,大多数属于以下三类:运气够好,刚好认识对临床遗传学感兴趣的科学家;很有决心,最终找到了这些科学家;还有就是像黛比这样的家庭,参与了相关的研究项目。但现在,随着基因组测序的成本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高,世界各地都开始发起临床项目,为那些可能因基因组测序而受益的人提供测序服务。美国Illumina公司不仅为许多研究项目提供测序仪器,还为患有重大疾病的人提供基因组测序服务,费用只需7 500美元。而对于癌症患者,只要10 000美元,就能同时测定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的基因组序列。
部分人认为,随着价格进一步降低,基因组测序和分析将会像核磁共振成像(MRI)一样普及。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的临床遗传学家戴维·比克(David Bick)说:“和其他医学检测一样,基因组测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事实也的确如此:与其他医学检测结果不同,基因组测序会提供一大堆难以解读的数据,其中有些信息并非诊断或治疗疾病所必需的,还有很多信息可能会泄露病人未来的健康风险。
而且从目前报道过的几个成功案例来看,从人类基因组中抽取信息,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充分的医学解读,对于目前已经捉襟见肘的医疗体系而言,可能是个过于沉重的负担。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NHGRI)所长埃里克·格林(Eric Green)说:“这些案例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但你不能仅仅因为这几个案例,就把基因组测序直接纳为常规检测。”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进一步研究。
测序是否必要
以尼古拉斯·沃尔克(Nicholas Volker)为例。从他出生开始,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就在蹂躏他的肠道系统,有时甚至造成瘘管(fistula,即穿透肠壁直通体表,并从中溢出粪便的漏洞),必须通过手术来修复。沃尔克三岁前,他就已经进出手术室上百次了。医生猜测,他可能有某种免疫缺陷,骨髓移植或许可以缓解病情。然而,对他进行多项检测(包括对多个基因的测序)后,医生仍无法确定病因。经过一番商议,威斯康星医学院的医疗团队终于获准对沃尔克进行外显子组(exome)测序。外显子组大约占基因组的1%~2%,负责编码蛋白质及重要的调控性RNA 分子。
借助计算机工具,该医疗团队仔细分析了沃尔克的DNA序列,以期找到不同于其他个体的序列。威斯康星医学院的临床遗传学家戴维·迪莫克(David Dimmock)说,他们把沃尔克的DNA分别与普通人群中的已知突变、疾病相关突变以及其他物种的相关序列进行比较,寻找可能导致沃尔克所患疾病的基因突变,“如果是一个人来完成,这个工作量相当于他要盯着电脑看上三个半月”。结果,他们在X染色体上发现了一个基因突变。发生这个突变的基因会编码X染色体连锁凋亡抑制因子(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XIAP),如果该蛋白出现功能缺陷,就会极大增加免疫疾病的患病风险。基于这个原因,沃尔克只有接受骨髓移植才能缓解病情。手术一年多后,沃尔克恢复得还不错。
这个由莫迪克、比克及其同事在威斯康星进行的实验,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致力于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基因组测序。他们主要针对那些疑似患有罕见遗传病的个体,希望能通过基因测序,确定病人的遗传缺陷,协助疾病治疗。
比克说,48位病人曾申请参与这个项目,17位通过评定,已被接受参与实验。在测定基因组序列前,他们的家属也要接受遗传咨询。一些保险公司已同意,至少为两个病人承担所需费用。提供测序服务的则是Illumina公司的临床服务实验室。该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蒂娜·汉姆布赫(Tina Hambuch)说,保险公司愿意为病人埋单的原因很简单:与一系列遗传检查相比,全基因组测序可能更便宜,而且可以让他们知道病人所要求的昂贵治疗是否必要。“因而为此付出一些成本其实很划算”。
风潮与局限
其他研究机构也开始跟进测序项目。在英国,牛津大学维康信托基金会人类遗传中心计划与Illumina公司合作,为500名患有不同疾病的人测定基因组序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08年推出了 “疑难病症研究计划”,其中就包括一个测序项目。迄今,该项目的科学家已测定过140个外显子组和5个基因组的序列,希望弄清楚导致疑难病症的分子基础。这个项目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多数病人都想参与,项目组不得不在几个月前暂停接受申请。
NHGRI所长格林认为, “现在是推动基因组测序的时候了”。遗传学家经常会谈论孟德尔遗传病(Mendelian disorder)的治疗:凡由单个基因突变引起,大致遵循孟德尔遗传定律的疾病都属此类。在全球住院治疗的儿童病例中,多达20%的患儿都与孟德尔遗传病有关,治疗这类疾病的费用也在医疗保健支出中占了很大比例。但这些疾病的遗传基础通常不明确。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OMIM)收录了近7 000种遗传疾病,其中大约只有半数疾病的分子致病机理是已知的。
但仍有很多人担心,大多数基因组信息都难以在临床上发挥作用。在“疑难病症研究计划”中,失败多过成功。NHGRI医学遗传学部门的托马斯·马科洛(Thomas Markello)说,“分析外显子组非常困难。现在我最担心的是,公众并没有意识到,迄今发布的研究报告都只提到了成功案例。”
很多研究者认为,基因组测序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中可能更易发挥作用。医生已经开始对某些肿瘤进行精密分析,根据病人的遗传特质制定疗法,而基因组测序能为医生提供更多遗传信息。有时,患者的癌症基因组信息能告诉我们这种癌细胞在某一生物途径中所存在的缺陷,医生就能针对性用药,有效改善由该缺陷引起的病症,而一般检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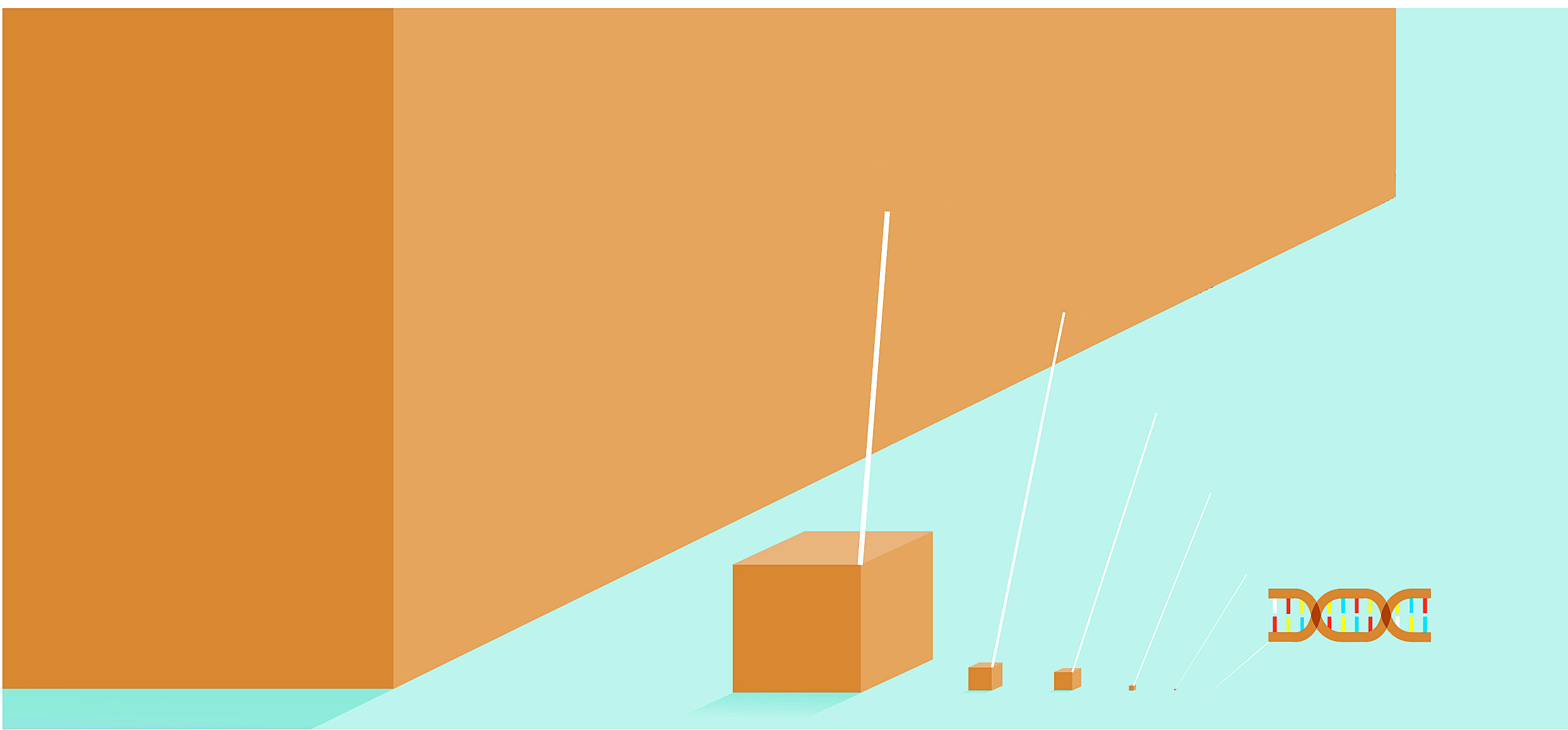
2007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所(British Columbia Cancer Agency)收治的一名78岁老人患了一种罕见舌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当时,市场上还没有获准治疗这类癌症的药物,但在这位老人和医生的请求下,研究所的科学家测定了老人癌细胞的基因组序列,还分析了转录组(transcriptome),确定了癌细胞中RNA的序列和数量。然后,他们把这些数据与其他癌细胞和病人正常细胞的相关数值加以比较。
通过分析,研究人员注意到了RET基因。这个基因是已知的促癌基因之一,在老人癌细胞的基因组中,该基因有两个拷贝,由此转录生产的RNA分子数量也是正常细胞的两倍。对于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当时好几种药物都可以抑制它的活性。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所基因组科学中心的负责人马科·马尔拉(Marco Marra)说:“我们的临床研究小组比较了候选药物的各种性质,最后筛选出了疗效最好的舒尼替尼(sunitinib)。”经过头两次治疗,老人的病情稳定了好几个月,但后来癌细胞又开始扩散。研究人员又进行了检测分析,发现这些癌细胞中的另一条促癌分子途径被激活,因此舒尼替尼失效了,但其他药物可能有效。不幸的是,治疗已没法继续:老人去世了。
担忧与趋势
目前,马尔拉的团队正在筹划一个新的研究项目,利用转录组和其他测序方法,更准确地诊断不同类型的急性粒细胞白血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遗传学家伊莱恩·马蒂斯(Elaine Mardis)受到马尔拉的启发,也与合作者利用基因组测序,为多位癌症患者提供帮助,其中包括一名患有白血病的妇女。这位患者接受治疗后,旧病复发,但常规检测无法确定,复发的白血病是常规疗法就能控制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还是需要后继治疗的其他白血病。随后7周,马蒂斯的研究小组对患者的癌细胞基因组进行测序,发现了APL特有的基因融合现象。虽然热衷于这种方法,但马蒂斯也特别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这项技术为疾病诊断提供了又一个依据,但绝不能把基因数据看成唯一的诊断标准。”
要把基因组测序从研究转入临床,需要面对很多挑战。与研究不同,作为诊断依据的DNA 测序必须由获得认证的实验室来完成。负责监管人体研究的机构审查委员会,还没有就临床基因组测序是否需要通过审批达成共识;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对即将到来的临床测序风潮,也还未出台相关监管条例。
许多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还担心,在目前医疗卫生系统中,精通基因组学或生物信息学的工作人员不够,难以应付大量的数据分析。一些专家说,目前有关人类基因组功能和相关疾病的信息,零散地分布于各种科学论文和数据库中,不但很难查找,有时还是错误的。而序列分析则是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汉姆布赫表示,在Illumina公司参与的几个研究项目中,仅仅确认一个基因组中的基因突变,就需要2~3周的时间。“这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工作量庞大、需要多人协作的环节”。
基因组信息还可能让病人受到打击。医学遗传学家和伦理学家一直担心,基因测序会发现一些与当前疾病无关,但会反映其他患病风险的遗传指标。随着全基因组测序的普及,这样的发现会越来越多。对于年轻病人,这种情况尤其棘手。父母是否有权替他们决定公开哪些遗传信息?比克说,这就是为何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遗传辅导上的原因。
基于这些原因,美国仁爱儿童医院(Children’s Mercy Hospital)的斯蒂芬·金斯莫尔(Stephen Kingsmore)认为,临床测序应在特定范围内进行,只对那些已知的、与遗传疾病相关的基因区域(即所谓的孟德尔组,Mendelianome)进行测序。 “无论从伦理学和法律,还是社会学角度,这种测序方式都更容易为人们接受。”目前,他的研究小组就在研究一些方法,在与600多种隐性遗传病相关的基因突变中,筛查某种疾病的致病因子。他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是把研究利益放在病人利益之上。
然而,一些遗传学家却认为,基因组测序进入临床是无法阻挡的。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哈康·哈科纳森(Hakon Hakonarson)正在开展一个基因组临床评估项目,他谈道:“一旦人们知道基因组测序会带来多少信息,这种技术必将被广泛采用。”
黛比和家人仍在思考,对他们而言,基因组序列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目前的治疗方案不会因为基因组序列而改变,但如果早一点知道希瑟和罗根的肺部问题,他们或许就不会去做那种危险手术来阻止肺炎复发。
林恩·约尔德认为,基因组测序的很多好处会在临床医疗中渐渐体现出来。“我预计基因组测序还会有很多了不起的应用。不过,我也承认我向来是个乐天派”。
本文作者 布雷登·马赫是《自然》杂志编辑。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