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迷幻剂平反
撰文 罗兰德·R·格里菲斯(Roland R. Griffiths)
查尔斯·S·格罗布(Charles S. Grob)
翻译 张嵘
2004年春天的一个早晨,50岁的女教师桑迪·伦达尔(Sandy Lundahl)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行为生物学研究中心报到,自愿成为美国30多年来首个迷幻剂研究的受试者。她完成了问卷调查,与两个将在随后8小时内全程陪同她的监控者闲聊着,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起居室的舒适房间——试验将在这里进行。伦达尔吞服了两粒蓝色胶囊,躺在一个沙发上。为了放松和集中精神,她戴上眼罩和耳机,听着一段特意挑选的古典音乐。
胶囊里含有高剂量的裸盖菇素(psilocybin),这种化学物质是“魔幻”蘑菇的主要成分,跟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和酶斯卡灵(mescaline)一样,能使人的情绪和感知发生变化,但很少产生真正的幻觉。试验最后,当裸盖菇素的药效消退时,以前从未服用过迷幻剂的伦达尔填写了调查问卷。从她填写的答案来看,呆在试验房间的这段时间里,她有过一种极为神秘的体验,就像在各个时代很多文化都描述过的追寻精神家园的人那样,感觉与所有人和物联系在一起,还伴随着仿佛在穿越时空、极度快乐、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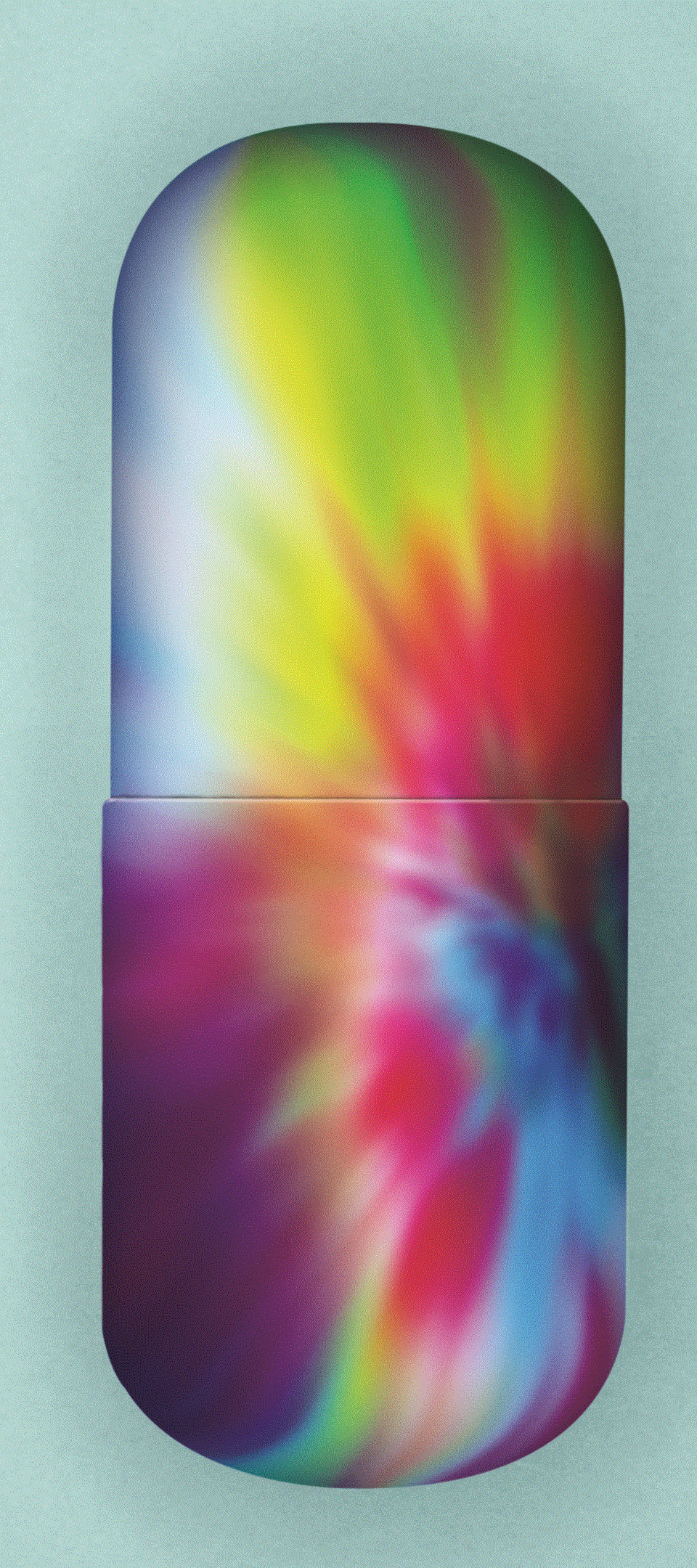
一年多后,在一次随访中,伦达尔说她每天都会回味那次经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甚至把它当作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精神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她觉得这次经历使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行为都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对人生的满足感也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次经历似乎使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她写道,“新的感悟不断从脑袋里冒出来……我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它弥补了我曾受到的伤害,我越来越能发现人性的优点。”
除了伦达尔,本文作者格里菲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的研究还有其他35名受试者。这项研究始于2001年,2006年发表研究结果,2008年又发表了一篇后续报道。当第一篇报道出现在《精神药理学》(Psychopharmacology)杂志上时,很多科学家都表示:很高兴看到这个已沉寂多年的研究领域“复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裸盖菇素的研究一直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监测裸盖菇素对健康受试者精神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同时也在探究这种药物引起的意识状态变化(尤其是那种神秘体验)能否缓解精神和行为障碍,包括那些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在这些研究中,裸盖菇素是主要用药——它是一种经典迷幻剂。与LSD、酶斯卡灵、DMT(对苯二甲酸二甲酯)等同类的其他药物一样,裸盖菇素的作用目标也是大脑细胞上负责与信号分子5-羟色胺结合的受体。容易让人混淆的是,在大众媒体和流行病学报告中,其他一些类型及药理效应都与经典迷幻剂不同的药物也被贴上了“迷幻剂”的标签。不过,这些药物中可能也具有药用潜力,比如克他命(ketamine,一种高效麻醉剂)、MDMA(摇头丸)、二萜内酯(salvinorin A,提取自墨西哥的一种“迷幻”鼠尾草)、伊菠加因(ibogaine,一种抗抑郁药)等。
一度中断的研究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就开始从一大堆研究中寻找迷幻剂可作为药物使用的证据,更有数以千计的自愿者参与到研究中。一些研究表明,迷幻剂有助于治疗药物成瘾,缓解临终病人的精神压力。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一些迷幻剂被当作毒品使用(主要是LSD),再加上大众媒体的过度渲染,迷幻剂相关研究被迫中止。而且在此之前,迷幻剂研究已经因为1963年的一个事件而声名狼藉:美国哈佛大学的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利用迷幻剂进行了一些极具争议的研究,比如阿尔珀特曾在校外给一位学生服用裸盖菇素,这两位科学家被哈佛大学开除。这一事件在当时被炒得沸沸扬扬。
或许是由于利里对迷幻剂的公开支持具有太强的示范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滥用这种化学物质,尽管人们对它的了解少得可怜。这终于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应。1970年,美国《物质管制法案》(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将迷幻剂纳入I类物质,也就是限制最严格的那一类。政府对迷幻剂的人体试验也设置了新的限制,并且终止了经费支持。从事这类研究的科学家突然发现,自己的研究领域已被边缘化。
当阻碍迷幻剂研究的种种担忧像浮云一样飘散,科学家又可以对这种闻名已久的化学物质进行严格的人体试验时,几十年过去了。迷幻剂给人带来的那种神秘体验让科学家很感兴趣,主要是因为这种体验也许能使人的情绪和行为产生快速而持久的变化——如果使用传统心理疗法,这种变化要花多年时间才能实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那项研究之所以让人兴奋,是因为它证实了,这种体验可在实验室中大多数受试者身上诱导出来。科学家第一次可以对迷幻剂进行严格的、可预期的科学研究——追踪观察受试者服用迷幻剂前后的表现。通过这些研究,他们可以弄清楚这种非凡体验的成因以及它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在最近的研究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使用的一些调查问卷,原本是为评估自然发生(不用药诱导)的神秘体验而设计的。他们还用这些问卷从总体上评估受试者服用裸盖菇素2~14个月后的心理状态。数据显示,受试者的自信心、内心的满足感、承受挫折的能力都增强了,而紧张和焦虑情绪则有所缓解,健康状况有了整体提升。而且,亲朋好友对他们的评价(事先不知道受试者服用过迷幻剂)与他们的自我评价是一致的。一位受试者对那种体验的经典评论是:“我有种万物归一的感觉,似乎体会到宇宙的真谛,明白了上帝对我们别无所求,只接受爱。我并不孤单,也不惧怕死亡,我很喜欢现在的我。”另一个受试者更加富有灵感,竟然将这种感受写成了一本完整的书。
戒毒良药?
当年,迷幻剂相关疗法的研究还未被喊停时,科学家想用它来对付的目标就排了长长一串:酗酒、药物成瘾、癌症伴发焦虑、强迫症、创伤后应激障碍、身心失调、严重性格异常、自闭症……但在当时,公开发表的大部分论文都像是猎奇报道,罗列的实验数据远没有对照性临床试验可靠。在那段时期,就是最好的研究都没有设置严格的对照试验,更没有使用现代精神药理学研究中的那些标准方法。
癌症患者常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情绪和抑郁症状,抗抑郁药和缓解焦虑的药物对此都没有太好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在一系列临床试验中,共有200多名癌症患者服用过经典迷幻剂。196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埃里克·卡斯特(Eric Kast)在一项研究中,给疼痛难忍的晚期癌症患者服用了LSD。他在后来的研究报告中写道:这些患者“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似乎对眼前的悲惨遭遇毫不在意,能够坦然地和他人谈论即将到来的死亡。在西方人看来,这种态度不合时宜,但对患者的心理状态有百利而无一害”。随后,美国斯普林·格罗夫州立医院(Spring Grove State Hospital)的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Stanislav Grof)、威廉·理查兹(William Richards,他和格罗夫后来又去了马里兰精神病研究中心)和同事又利用LSD和另一种经典迷幻剂DPT(dipropyltryptamine,二丙基色胺)做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这些迷幻剂能缓解病人的抑郁、焦虑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而且有过神秘体验的病人在心理健康上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
本文作者格罗布为这类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2010年9月,《普通精神病学文献》刊登的一篇文章,报道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海港医学中心在2004年至2008年所做的一项初步研究,目的是评估裸盖菇素能否减轻12名晚期癌症患者的焦虑情绪。尽管这项研究的规模太小,难以得出明确结论,但结果令人鼓舞:即使试验结束已有几个月,癌症患者的焦虑情绪仍有所减轻,心情也明显好转。而且与多年前所做的研究一样,这些患者对日益迫近的死亡也不再那么恐惧。现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大学已经在一些研究中,给癌症患者使用更高剂量的裸盖菇素,以便更容易诱导出那种神秘体验——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体验是产生持久疗效的关键因素。在瑞士,一项类似的初步研究也已开始,只是该研究使用了LSD,而不是裸盖菇素。
据报道,酗酒者、烟民和其他物质滥用者有时会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自发产生一种刻骨铭心的神秘体验,从而使自己爬出成瘾的泥沼。在迷幻剂的第一波临床研究中,科学家就注意到了这种能改变人们心理和行为体验的潜在疗效。数十年前,共有1 300多位病人参与成瘾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超过20篇。在某些研究中,受试病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心理支持,在他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就开始给这些病人使用高剂量的迷幻剂,少数病人甚至被绑在自己的床上接受试验。那些认识到病人在不同环境、心理和生理状态下会对迷幻剂作出不同反应,以及会给病人提供更好心理支持的研究人员,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研究结果。总的来说,这些早期研究虽然让人看到了希望,却没能得出明确结论。
由于研究方法上的进步,新一代迷幻剂研究应该能确定这类药物到底能否帮助人们戒掉毒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格里菲斯、马修·约翰森(Matthew Johnson)和同事已开始进行一项初步研究,希望用裸盖菇素辅助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即教会病人如何改变想法和行为以戒除不良嗜好,并保持下去),帮助烟民戒除烟瘾。
除了治疗成瘾,近期一些研究也开始测试裸盖菇素是否有助于缓解强迫症。其他一些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管制药物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医用潜力。最新研究显示,比起百忧解之类的传统抗抑郁药,低剂量的克他命(一般作为麻醉品)能更快缓解抑郁症状。最近,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中,MDMA成功治愈了一些传统疗法已无能为力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瑞士和以色列也在开展类似的MDMA研究。
未来风险
想让经典迷幻剂相关疗法获得认可,科学家必须消除迷幻剂过量可能导致的副作用。有时,迷幻剂会使人感到焦虑、恐慌或者疑神疑鬼,如果在无人监控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意外伤害或自杀事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的那项研究中,即使有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提前为受试者做了8小时的心理疏导,而且研究全程处于严格监控下,仍有1/3的受试者在某一时段感到特别恐惧,1/5有时会疑神疑鬼。不过在研究中心,实验室的设置有家一样的感觉,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也始终在对受试者进行引导,这些受试者的病态症状并没有持续出现。
使用迷幻剂还有其他潜在风险:精神病症持续出现、精神压力增大、连续数天甚至更长时间出现视觉错乱或其他感觉紊乱。这些副作用并不会经常出现,如果让受试者做好心理准备,并接受严格监控,他们就更不容易出现上述症状。尽管迷幻剂有时会被滥用(以一种可能危及使用者自身或他人安全的方式使用),但通常来说,这些药物并不能看作成瘾性毒品,因为它们既不会让使用者欲罢不能,也不会导致戒断综合征(withdrawal syndrome)。为了尽可能减少迷幻剂的副作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小组最近发表了一份安全指南,供进行高剂量迷幻剂研究的科学家参考。假如研究人员有能力控制使用迷幻剂的风险,我们认为这类研究应该继续下去,因为迷幻剂有可能改变一位癌症患者或吸毒者的一生。如果研究证实,迷幻剂确实有助于吸毒者戒掉毒瘾,缓解病危患者的焦虑情绪,科学家下一步就可以探索,迷幻剂诱导的那种神秘体验能否融入重大公共健康问题的相关疗法,用于治疗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高风险性行为或更多适应不良性行为(maladaptive behavior,如恋物癖、露阴癖、异装癖等)。
上世纪60年代,大脑成像以及一些药理学技术都还不存在。这些技术的出现无疑会加快迷幻剂研究的进程,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这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人们服用迷幻剂后,对那些与思维和强烈情感相关的脑区进行成像,科学家就能弄清迷幻剂到底触发了哪种生理机制,导致人们产生了那种神秘感受。更深入的研究可能还会催生一些非药理学手段,能更快生效,功效也比冥想之类的传统精神疗法好。换句话说,这些治疗手段能很快让人产生那种神秘感受,使行为恢复正常——上世纪30年代,正是这种感受使得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决定与美酒决裂,创办戒酒互助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
弄清楚神秘体验如何使人们更好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反过来有助于解释精神力量对于心理健康的保护性作用(这种作用已得到充分证实)。神秘体验能产生一种深刻而持久的感受,让人们认为自己与所有人和物联系在一起——这种想法是世界所有宗教和精神文化的道德体系的基础。知道了经典迷幻剂的生物学机理,就有助于阐明人类道德与协作行为背后的机制——我们相信,这种认识最终可能将会成为整个人类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查尔斯·S·格罗布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格芬(David Geffen)医学院的精神病学与儿科学教授,也是该分校海港医学中心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分部的负责人。他用多种迷幻药进行过临床研究,比如使用裸盖菇素治疗肿瘤患者的焦虑症状。

罗兰德·R·格里菲斯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与神经科学系的教授,他主要研究精神调节药物的精神与行为学效果,目前他也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裸盖菇素研究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