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100年和150年之后,人类预计会在科学领域取得哪些里程碑式的成就?每过一个月,我们就向未来更进了一步,就能又一次回顾往昔,看看50、100和150年前的科学家写了些什么(见本刊每期“经典回眸”栏目)。
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168年以来,《科学美国人》杂志始终让它的读者身处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我们1962年10月的杂志,刊登了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撰写的深度报道,介绍了这一令人惊奇的分子的重大意义;除此之外,还有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文章,介绍他所谓的“认知失调”究竟为何。历史,永远像明镜一般照向未来。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要求以下文章的作者将目光和想象投向距今天50、100和150年之后的未来,描述一下那时的世界是什么模样。汽车能飞了吗?我们还在使用计算机吗?如果是的话,那时的计算机都能做些什么?核武器会全部销毁吗?我们新研发的技术能最终阻止气候变化吗?还是反而让事情更糟?在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地球上,老虎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操控自己的基因?这能用来预防疾病吗?还有,我们最终能离开地球吗?这样的星际旅行将如何改变我们?……在接下来的几页里,你们将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并非答案,因为我们不是在预测,而是在进行“思想实验”:基于科学事实,通过观察今天的世界,对未来世界的模样进行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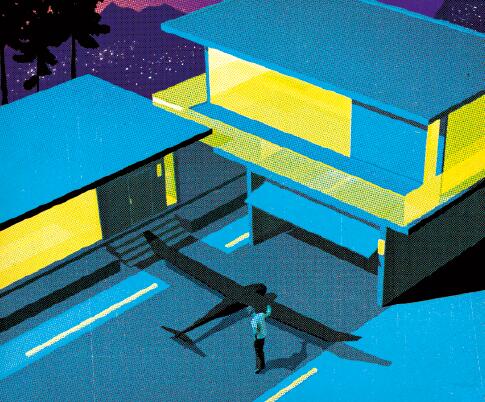
1956年,随着飞行车Aerocar取得了美国民用航空管理局颁发的适航证书,这类飞行车似乎即将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居住在大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必备交通工具,至少在航空工程师们看来是这样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Aerocar看起来像一辆带有翅膀的汽车,能从较短的跑道起飞。由于价格太高而不适于大规模生产,Aerocar国际公司只生产了6辆这样的飞行车。飞行车大行其道的愿景变成了泡影,我们只有在电视剧《杰特森一家》(The Jetsons)中才能对那样的世界略见一斑。
然而50多年以后,飞行车又强势回归了,有两种型号的飞行车已经完成了至少一次飞行测试。其中,美国马萨诸塞州的Terrafugia公司设计制造了“Transition”飞行车,这是一部轻型运动航空器,具有可折叠机翼,可乘坐两人并有相应的行李舱。要想起飞,首先你要把它开到机场里(它需要普通的跑道来起飞)。另一种飞行车是荷兰PAL-V欧洲公司设计制造的PAL-V(个人空地两用车,personal air and land vehicle的英文缩写)一号飞行车,起飞距离只有650英尺(约200米)多一点点。这种飞行车看起来就像是三轮车与直升机的“杂交”产物:飞行的推进力来自安装于尾部的螺旋桨,顶部还有一个能够自由转动的旋翼来产生升力。这两种飞行车的巡航速度均不超过100节(约185千米/小时),满油航程也都还不错(Transition是450英里,约合724千米;PAL-V稍逊,为300英里,约合483千米)。
不过,这两种型号都无法满足大规模生产上市的要求。就算生产商能将目前约30万美元的预期售价降低,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它们的市场仍然很有限,而究其原因,恰恰是由于未来愿景中,大量个人飞行器在天空和道路之间穿梭往来的画面——目前,仅仅是协调引导数千架飞机的起降,各个机场已经忙成一团了。如果到时每辆汽车都能飞了,天空中只能是乱成一锅粥。
目前,飞行车可归于“轻型运动飞行器”之列,任何持有有效驾驶执照的人都能驾驶这类飞行器,只要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而且拥有“运动飞行员”认证资格就行(仅需20小时的培训)。由于是“轻型运动飞行器”,这类飞行器需要避开拥挤的空域,而且只限于个人使用:即拥有这类飞行器驾驶执照的人,不允许开展商业飞行。
此种认证方法起作用的前提是:自驾飞行车的只有少数人。如果数量可观的驾驶员纷纷飞上天,空中交通堵塞可是很危险的。在真正被整合进入全国性的空域之前,飞行车的定位必将继续面向小型目标市场。
为了实现飞机走进千家万户的交通革命,我们必须放弃对操控的渴望,让飞机带着我们自动飞向目的地。个人用或商用飞行器将必须类似无人驾驶飞行器(unmanned aerial vehicles,缩写为UAVs,或称为无人机)。
在军队里,操控无人机的人或许从未取得飞行员认证。实际上,无人机最吸引人的优点之一,就是它们让军方得以节省培训飞行员所需的大把资金和精力。
今天的无人机智能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它们不仅能够飞到为它们预先设定的地点,并且,一些研究还将赋予它们拟人化的推理分析能力,以在紧急情况下自主作出反应。类似的思路同样被应用在了谷歌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上。考虑到通常会导致驾驶员分心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在驾驶中(和飞行中)聊天、发短信和吃东西等常见“喜好”,能够自动驾驶和飞行的汽车应该会让未来的交通运输更加安全。
要想实现这个愿望,即研制出一种能够投入市场的、经济便捷的载人无人驾驶飞机,仍面临着许多技术挑战。例如,必须建立起可靠安全的通信网络和稳妥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以在飞行车的航线上为其提供导航。
我们还需要将这些系统整合入全国性的空中交通管制网络,使其作为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到许多对现行空中交通系统进行大改的动议一次次失败,这也许是建立全国性个人空中交通系统过程中最棘手的障碍。不过,最基础的技术“部件”倒是现成的:近年来世界各地无人机的使用经验,就为我们提供了50年后个人空中旅行的模型。目前,我们必须找到将所有这些技术“部件”拼接到一起的方法。
201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上马了一个名为“变形金刚”的项目,旨在设计建造一种能乘坐四人、适于上路,并能够垂直起降的车辆(实际上就是一种载人无人驾驶飞机)。不具备航空飞行背景的普通士兵就能够操纵它,甚至比操控现有的无人机更简单。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期望,这种车辆的原型机能于未来数年内试飞。随着此类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如Transition和PAL-V这样,代表着空-地两用车最先进技术的商业化个人航空器的出现,在未来的50年里,我们将很有希望看到家家都有飞机的那一天。50年后的乔治·杰特森(《杰特森一家》中的人物),就能乘坐着无人驾驶飞机到处旅行了。
本文作者:玛丽·康明斯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副教授兼人类和自动化实验室主任。
核武迷思
如果世界无法在本世纪中期放弃核武器,我们也许将面临灾难,本文以虚构的方式,探讨了核武器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撰文: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nbaum) 翻译:戚译引

2063年8月8日,核裁军决议日(Nuclear Disarmament Decision Day)。当我们以这个视角回顾过去,2024年的第一场“小型”核战争的起因依旧无从得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一旦发生,一切就改变了。幸存者们发现,核战争不再只是个传说,核灭绝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可能。真相逐渐显露出来:警告可能无效,事故可能发生,恐怖分子可能会偷走导弹弹头。来源不明的炸弹可能无端爆炸,引起大火。死亡人数可能多达10亿。核裁军似乎是避免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将导致全球性的物种大灭绝。
大约半个多世纪前,包括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内的一些核战略家打破传统,呼吁全球废除核武器,这让他们的同行大跌眼镜。这个举措现在被称为全球零核倡议(Nuclear Zero),这个倡议已经提出了50多年的时间。现在,一切终于就绪,核裁军的决议,或许在几分钟后就会出台。
核裁军的最终部署已经安排好了,就像在过去10年里人们所呼吁的那样。这次核裁军计划考虑得极其周详,包含了所有的监督和强制执行草案,保证了核裁军能全面、彻底、全球同步开展,保证了没有人能玩猫腻、隐藏核武,然后用剩下的这些核武威胁、统治那些因为相信核裁军计划而彻底放弃核武的国家。
不过,还是有一些“未知的未知”需要应对。这个计划真的万无一失吗?所有人都可以信任吗?会不会有一些核弹级别的核材料避开了高度发展的全球卫星监视和监测系统的搜寻?会不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国家拆开了他们的核弹,但随时会把这些零件重新组装成核武器,造成我们担心的“大爆发”场面?
2063年,所有已知的核国家都已把自己的军火储备缩减到了最小。这段时期是对“最终放弃”口号的呼应,已知核国家在密切监视下同步拆除、摧毁和废止所有剩余的核武器。
回到2011年,一个悲观主义者写道:“只有某种能改变人性的东西能让世界清醒过来,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和核武器不能共存。这也许是一场核战争,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它的规模会比较小。”
战争曾经爆发过,我们确实很“幸运”——这场战争的规模相对较小。但人性真的有了足够大的变化吗?
当那个时刻越来越近,全世界的屏幕都聚焦到了最终会议的主席台上。核国家的首脑们就座了。一些与会代表回顾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个个里程碑。一张纪年表如下展开:
2018年5月5日:美国和俄罗斯于2011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的核武器削减条款终于生效,双方的核弹头数量都下降到了1 550个。
然而,在和其他已知核国家进行的新一轮谈判中,削减核武器的努力在某些方面遇到了阻碍,比如有国家依然认为反弹道导弹系统很重要;美国参议院反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鹰派政客仍然梦想着构建“星球大战”系统;俄罗斯国防部中反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鹰派分子还是想开发新一代的多弹头导弹。给谈判带来困难的还有希望继续增强自身国防力量的新兴国家。
美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重要核国家也没有试图签订新的武器削减条约,或商议缩短警告时间,把井式导弹从发射井上取下。实际上,这种行为传递出的信号是,这些导弹是“一触即发”的,是对其他国家的一种警告:导弹很容易“无意”发射,形成核威慑或引发战争。相反,这两个国家花费数十亿美元建造反导弹防御系统。这些未被证实的威慑包括装备了核武器的卫星和“卫星杀手”,美国把它们部署在东欧,而俄罗斯把它们部署在北极地区。
2021年8月8日: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里,最恐怖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国际无政府主义精英组织“黑帽子”(Black Hat)入侵了美国蒙大拿州和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冰原上两个核导弹地下井的控制系统。
两个发射点各发射了一枚导弹。没有人知道恐怖分子有没有掌握引爆密码,直到两枚导弹都落在了太平洋北部一块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大小的叫做“垃圾海”的区域,但没有爆炸。更麻烦的是,卫星导弹拦截系统拦截它们时偏离了好几千米。于是,没有一个国家知道还能不能信任它们的C3系统(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
计算机系统已经成为悬在世界上方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024年8月:剑落了下来。每个人都认为交战的可能是伊朗和以色列,或朝鲜与韩国。在21世纪初发生了几次激烈冲突之后,战争终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一颗原子弹在孟买爆炸了,而关于这个原子弹的信息只有一封无迹可寻,而且可靠性不明的电子邮件。印度政府把此事归咎于巴基斯坦的一个恐怖组织,于是双方都决定先发制人。
我们至少知道核战争是怎么样的了,它比想象中更惨烈。被熔化的躯体和被辐射烧伤的孩子们的哭号声让所有人大为震惊。《科学美国人》在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评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场“小型”核战争(相当于使用50~100个广岛原子弹)爆发的结果,最终居然一语成谶:2,000万人在爆炸中瞬间丧生,随之而来的是无法控制的大火和辐射污染(见《环球科学》2010年第2期《核冬天一触即发》)。
上述文章作者预言的核冬天不幸变成了现实。烟尘被爆炸和大火推进高层大气,形成了一层致命的烟幕,笼罩在地球上空。严寒毁灭了大量的粮食作物,近十亿人死于饥饿。
还有几百万人死于随之而来的电磁脉冲。这是原子弹在较高层大气中爆炸产生的结果,它摧毁了电网,让三个大洲陷入了恐怖的黑暗。地球上大片大片的地区开始失控,随后瘟疫和暴力统治横行,许多地区大面积地倒退回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2031年:文明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始复苏。在这个饱受核战创伤应激障碍困扰的地球上,如果无视核武器废除条约,还是像往常一样发展核军事力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久存在。
但这有用吗?人类的本性是否发生了改变?
2035年3月:按照早在2010年制订的全球零核倡议的4阶段计划,第一份全球核裁军条约签订。当然,细节决定成败,但在辐射和瘟疫横行的时候谁还管那么多呢?这一次,我们过于相信信任,相信条约会生效,它也必须生效;相信没有人会作弊;相信信任能够被验证。
巡查、监视和执行方面的技术有了进展。精妙异常的大脑扫描系统被植入每一个核工作者的大脑,以发现阴谋。卫星的下视/下射反导弹能力已经得到了证明。星战系统变成了现实,而且它的运行必须绝对可靠。
2049年6月:地球上每个核国家都把自己的国防力量削减到12枚核弹以下,并公开了自己可用于制造核弹的放射性燃料的数量。这些燃料都会上交给全球核销毁委员会。委员会拥有严苛而先进的监测技术、装备了传统武器的强大军事力量。
武器削减的计划是,在2055年之前将武器减半,在2060年再将剩余量减半。
2056年12月,最后一块拼图就位。卫星无法发现潜行在深海的核潜艇,这一直是一块顽固的技术性绊脚石。现在,新一代的卫星激光器终于实现了“让大海透明化”的理想。没有潜艇能够对它隐形——我们希望这样。
全球性的监视和部署系统能否发挥作用?它能不能在任何一个国家藏匿什么危险资源之前生效?废除核武器会不会让传统战争更容易爆发,并让在传统战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更倾向于改用核武器?
2063年8月8日:至少我们快要知道答案了。这一刻终于来临。这是有史以来赌注最高的博弈。核国家的首脑围坐在会议桌旁,仅仅是为了按下一个按钮,通过最终部署(如果其中任何一方要摧毁剩下的核弹头,需要所有人按键表决)。首脑们都在微笑着。
迟早,或许更早一些,我们就能知道某个微笑的后面有没有隐藏什么东西。验证这个系统是否万无一失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许多年,也许是永远,如果人性不会改变。
本文作者:罗恩·罗森伯姆(Ron Rosebaum)是一位科学作家,出版了7本书,他的最新作品是《终结的开始:通往第三次世界核战之路》(2011年由Simonand Schuster出版社出版)。
基因疗法照进现实
50年后,基因疗法的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医学,人类在医疗上的支出将会锐减,很多人都会健康长寿。
撰文:里奇·路易斯(Ricki Lewis) 翻译:褚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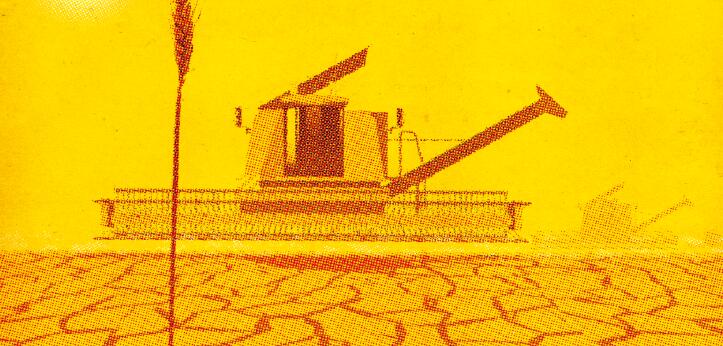
时间:2063年。你走进一家诊所,护士从你身上取了点儿唾液、血液或胎儿细胞(prenatal cell)作样品,然后放入一枚微芯片中进行检测。微芯片只有这页纸上的一个字那么大,被装在一部手持设备上。微芯片发出的各色荧光表示,在你的DNA里,存在着一些基因序列,它们会导致,或者影响某些单基因疾病——这样的疾病有1 200多种。幸运的是,监管部门已经批准了一种疗法,用来对付所有这些疾病——它就是基因疗法。
基因疗法的具体机制是,利用一种病毒天生就有的“生物机器”,将健康的基因载入细胞核内,替换掉导致疾病的突变基因。这种想法其实早已有之,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不久,就有科学家提出了这种设想。只是,在通往最终目标的道路上,却布满了荆棘。初期的一些尝试最多只能算偶有成功,更多的是失败。1999年,一位18岁的年轻病人在接受基因疗法时死亡:这位病人患有一种代谢疾病,而这种疾病又引发了一种致命的免疫反应;当科学家利用一种病毒,实施基因疗法时,结果这种病毒却在病人肝脏的免疫细胞中引发了一种免疫反应。也是在1999年,两个婴儿接受了以逆转录病毒为载体的基因疗法,用以治疗一种遗传性免疫缺陷,结果逆转录病毒携带的基因最后变成了致癌基因,使这两个婴儿患上了白血病。
这些挫折让基因疗法陷入困境,科学家也为应该以何种病毒为载体,才能安全地把治疗性基因转入细胞而争论不休。
一个艰难的开头之后,基因疗法触底反弹,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2012年,欧盟委员会批准了首个基因疗法,用于治疗脂蛋白酯酶缺乏症(患有这种疾病的人通常无法消化脂肪)。
两年后的2014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接连批准了3种基因疗法,分别用于治疗遗传性失明(利伯氏先天性黑内障,leber's congenital amaurosis)、一种免疫缺陷(腺苷脱胺酶缺乏症,adenosine deaminase deficiency)、一种影响脑部健康的遗传疾病(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adrenoleukodystrophy)。这些疾病尽管罕见,但相对容易锁定药物作用目标。
这些药物得到上市批准,肯定了腺相关病毒(adeno-associated virus,AAV)是可以作为基因载体的。实际上,大部分人的细胞都携带有这类病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容忍它们,对它们“视而不见”。相反,尽管逆转录病毒经过改造,会在人体内“自杀”,但仍会导致癌症,就像1999年那两个婴儿的遭遇一样。至于慢病毒,虽然曾经获得过FDA的批准,但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因为病人不愿意医生给自己注射HIV(HIV是慢病毒的一种),尽管这些HIV已经去除了导致艾滋病的基因。
2016年,针对B型血友病的基因疗法的问世,证明了这种技术的经济价值:基因疗法是一次性的,仅需30,000美元,而传统疗法,也就是注射凝血因子,是终身性的,多年下来的总花费最终可能高达两千万美元。
我们能够控制人体对病毒载体的免疫反应,就意味着最大的技术障碍已经克服:注射到病人体内的“药物包”不仅能提供替代基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体对癌细胞和病原体感染的免疫反应,还能减弱人体对病毒载体的某些排斥反应。
现在,基因疗法的大门终于敞开了:由于视网膜是与免疫系统隔开的,因此针对100多种失明症状的基因疗法首先进入临床;2019年,10多名患有极为罕见的巨轴索神经病(giant axonal neuropathy)的儿童成为“先驱者”,接受了针对脊髓的基因疗法;接下来是脊髓损伤、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和脊髓性肌萎缩,纷纷为基因疗法所攻克。另外,通过静脉注射,携带着治疗性基因的腺相关病毒可以穿越血脑屏障,阻止帕金森病等脑部疾病的发生,治疗此类疾病再也不用像21世纪初那样,要在头部“打洞”了。
随着时间流逝,科学家会逐渐认识到,对于有些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不一定是替换基因。就拿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来说,利用药物,清理一些结构有误的蛋白可能更好一些,因为在肺部和呼吸道中,根本没有可以接受基因治疗的细胞。还有杜氏肌萎缩(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在小孩的身体中,重新激活“沉默”的基因,要比向每个肌肉细胞传送治疗性基因更容易一些。
基因疗法的不断成功,只会给这类技术开拓更大的施展空间。到21世纪中期,新的疗法将不止针对罕见的单基因疾病,还可治疗更常见的、与遗传和环境因素都有关的疾病,比如精神疾病、糖尿病以及大部分心脏病。
到2060年,人类在基因测试(结合遗传干预),预测未来健康风险上,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准确度,产生极大的社会意义。当疾病还在萌芽阶段就可以把它们消灭时,人类在医疗上的支出将会锐减,很多人都会健康长寿。
本文作者:里奇·路易斯是遗传学博士,最近出版了《永远健康:基因疗法与拯救它的孩子》(the forever fix: gene therapy and the Boy Who Saved it)。此外,她还出版几本遗传学教材。
生物大灭绝就在前方
一个世纪后,狮子、老虎、猎豹等大部分猛兽都只会存在于动物园,或者面积极小、可看做“准动物园”的野外环境中了。
撰文:托马斯·拉夫乔伊(Thomas Lovejoy) 翻译:褚波

1980年,我向时任美国总统卡特递交了一份报告,首次预测了物种灭绝的情况。在报告中,我提到,如果按照当时热带雨林被砍伐和破坏的速度,到2000年,将有15%~20%的物种会灭绝。我预测的数字和实际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偏差。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提供的数据估计,13%的鸟类,25%的哺乳动物,41%的两栖类动物可能面临灭绝。
现在,很多物种的状况,都可以用科学家口中的一个词来形容:“living dead”,即这些物种虽然还未灭绝,但已被判死刑——灭绝不可避免。一个世纪后,狮子、老虎、猎豹等大部分猛兽都只会存在于动物园,或者面积极小、可看做“准动物园”的野外环境中了。而同样的命运,也等待着犀牛、大象以及人类的近亲——大猩猩和黑猩猩。
在1980年的那份报告中,虽然我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对了数字,但对于导致物种灭绝的环境因素,却想得太简单了。从那时起,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就在不断增强,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中,物种入侵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一些。在大洋洲,棕树蛇(Brown Tree Snake)已经对岛上的鸟类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包括关岛秧鸡(guam rail);在澳大利亚北部,外来的凶猛动物已经造成一大批本土哺乳动物的数量大幅下降,面临灭绝的风险;在美国,我所居住的弗吉尼亚州北部,近几年出现了三个新物种:亚洲虎蚊、一种会破坏绝缘体的蚂蚁以及名为茶翅椿的臭虫。
自然界的栖息地已经大幅减少。在非洲,依然完好的热带草原已不到30%,非洲狮的数量已不足原来的10%。而其他的外在威胁,比如打猎,也影响着哺乳动物和鸟类的数量。因为垂涎犀牛角和象牙,非法盗猎非常猖獗,以至于国际警察组织已把打击非法盗猎列为重点工作。到了下个世纪,婆罗洲犀牛(Borneo rhino)距离灭绝将只有一步之遥,人们可能只能在书中的图片和博物馆的骨骼展览中见到这种动物了。
野生动物疾病也是一个麻烦。动物的迁移已经导致野生动物疾病增多。壶菌(chytrid fungus)是目前最大的一个难题,已在全球范围内导致很多两栖类动物的灭绝——尤其是在新世界(指西半球或南、北美洲及其附近岛屿)的热带地区,首次出现了所有两栖类动物都在消失的情况。两栖类动物的遭遇,会不会是噩运也会降临其他动物种群的先兆?如果这种大规模消失事件继续出现,我们必然会想到的一件事是,菲律宾鹰(Philippine eagle)、角雕(harpy eagle)等体型庞大的猛禽会不会也跟着消失。在非洲和亚洲,大秃鹫似乎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角色。
人类正在改变全球的氮循环。过去30年间,因为密集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自然循环里的生物活性氮一直在增多,影响到了水资源中的氧含量,威胁到鱼类和植物的生存。同样,碳循环也在发生变化,导致气候变暖和海洋酸化。
气候变化已经冲击到生物多样性。一些物种的年度生命周期已经发生改变,比如有些植物的花期提前,还有些物种开始迁移,寻找更适宜生存的气候环境,比如约书亚树(Joshua tree)目前就在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向外迁移。北极海冰的融化意味着,黑海鸽(black guillemot)不得不飞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北极鳕鱼,而到了新的地方,却无法顺利造巢。一些移栖种(migratory species),比如非洲的牛羚(wildebeest)和遍布美洲的黑脉金斑蝶(monarch butterfly)可能走向绝境。由于找不到冰凉的溪流和河流产卵,很多鲑鱼也可能灭绝。
目前,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场堪称“海啸”的大灭绝正在悄然发生,剧变即将到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已经适应了10,000万年以来比较稳定的气候,而这种气候将无法持续下去。地球上各种各样的生物,适应能力也有着自身的局限。生存在较高地方的物种暂时可以继续向更高的地方搬迁,但最终将无处可搬;生活在岛上的物种更为脆弱,一来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二来它们再也无法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
当全球气温比工业化之前高出1.5℃时——现在看来,这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局,珊瑚礁将不复存在,而珊瑚生态系统的核心、珊瑚和藻类间的那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将崩溃。北美西部的原始森林可能正处于一场剧变的临界点上:暖和的冬天、更长的夏天将有助于树皮甲虫(bark beetle)的生长和繁殖,很多树木将死去、干枯,最后森林终结于一场森林野火。
野火、森林被毁、气候变化,这三种因素的协同作用,将会达到一个“引爆点”,危及亚马孙流域南部和东部的热带雨林——比起单独的气候变化,三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会让这一天更快到来。实际上,在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8℃~0.9℃的当下,我们已经能感受到那种可怕后果已处于风雨欲来之势。在某个时间点上,原本一体的生态系统将会分崩离析,各个物种将会独自行动,自己去适应气候变化。幸存下来的物种将会形成新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很难提前预料的结果,对于人类而言也是一个很难应对的局面。
我们需要更理智一些。就现在而言,应该做的第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是,调整自身行为,努力实现生物多样性大会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给地球上17%的淡水生态系统和10%的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保护措施。减少人类对气候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一举措将惠及地球物种和生态系统。通过全球规模的生态恢复手段,我们也许能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降低百万分之五十(这个值就是现在的二氧化碳浓度,与能让珊瑚礁幸存的二氧化碳水平的差值)。
所有这些行动都需要政治力量的参与,要让全人类都认识到,应该把地球当作一个生物和物理系统来对待,要认识到地球生命的多样性,这种认识对于人类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作者:托马斯·拉夫乔伊是“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一词的提出者,也在保护生物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地球工程改变未来
太阳工程(Solar engineering)及其他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的新技术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是多么复杂,以及摆在我们面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下文描述了三个形成鲜明对照的幻想场景。
撰文:戴维·W·基思(David W. Keith) 安迪·帕克(Andy Parker) 翻译:高瑞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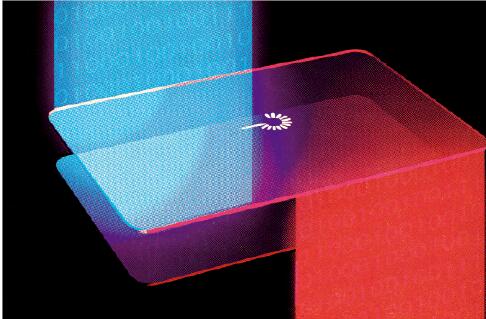
自然的末路
21世纪20年代的机器人技术革命催生了持续的经济繁荣,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于富裕的特大型城市,培养缸里生产出的转基因食品已经成为常态。大多数人与大自然之间失去了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联系:当你拥有计算机生成的感官模拟,并且配有设计药物,可以带来完美的体验时,谁还会需要真实的东西?只有纯粹主义者才会对野生动物和户外运动感兴趣,也只有他们还会选择“肉体性关系”。城市公园中,人造兰花芳香四溢。置身其中,回顾20世纪中叶的环保运动,似乎那只是对原始生活的返祖性渴望。碳排放量依然高歌猛进。
2047年,美国和欧洲决定实施太阳地球工程,即在大气层中喷洒颗粒物,使得部分太阳辐射发生偏离,从而降低气温。这项决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人类和自然的第三次大分离。
环保主义者和投资了北极(已无冰)石油勘探项目的能源公司组成同盟,激烈反对该工程。尽管如此,计划还是如期推进了。随后,环境灾难并未降临,这个项目最终赢得了认同。
巨大的气球升空,在平流层播撒下硫酸盐微粒,形成了包裹着整个星球的反射薄雾。城市居民开始享受到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例如农业生产力提高,食品价格降低。虽然农业和其他形式的生物生产力上升了,但生物多样性却锐减。这在海洋中尤其严重,因为二氧化碳导致海洋酸化,摧毁了大部分的珊瑚礁。这种精品店似的生态系统的消亡,是整个人类为了发展进步付出的小小代价。而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贫穷土著人则成为了最大的输家,他们缺乏保护自己权益的政治声音,进一步被边缘化。
21世纪末,全球气候委员会开始作出调整,降低极地和赤道的温度差异,从而在温暖气候影响下的地区培育新的经济活动。最终,气候协商变成了细枝末节的小事,环境问题也从报纸头条上撤了下来。因为各国都开始上演智能机器人的暴力叛乱,而且越发严重。至于最佳气候问题,也就仅限于在几个沉闷的专家委员会里辩一辩了。
2092年,里约+100环境纪念大会召开了。会址选在亚马孙河流域南部的军事基地。当年,第一批喷洒硫酸盐的太阳辐射管理气球就有部分是从这里升空的。现在,在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早已废弃的巨大建筑是周围原始风景上仅存的纪念物。
适应气候
承诺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那一直慢吞吞的进展,终于被发生在2018年的一系列事件催化、推动了。迟迟未至的东南亚季风,击垮美国东南部防洪系统的两场暴雨,再加上一次大旱,造成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损失。然而,最具冲击力的单幅画面,却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旗舰“彩虹勇士”三号径直穿过了没有冰的北极点——以前从未有船只到达过的地方。
经过了几十年徒劳的政治活动,最后,得到一个具有实际效力的气候条约却并不困难。2020年,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达成了框架协议,即温室气体排放在2035年达到高峰,此后迅速下降。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却遭到了一些政治力量的广泛攻击,他们说这是夺权。
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减排时,短期成本确实较高。但是人们逐渐看清,在总量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占不到全球GDP的3%。于是,政治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棘手的政策问题上,例如卫生保健支出,在2028年,这项支出已经上升到了美国GDP的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下出现了新的国际气候变化适应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Climate Adaptation Fund)。该组织有针对性地投资基础设施并提供小额信贷,从而为小规模的地方性措施提供便利,以解决气温上升引起的农业问题。这些努力在缓解气候变暖对人类的直接影响上起到了很大作用。
仅是适应气候变化有其局限性。由于碳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较长,气候系统本身也具有惯性,使得即使有了碳排放的分水岭协议,全球气温依然会比工业化前的平均水平提高多达3℃。全球继续变暖,海平面逐渐上升和日益加剧的极端天气事件也如影随形。
2040年,小岛国家联盟(AOSIS)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最终成功地说服了国际社会,开始实施地球工程。在一些经济强国的直接援助和其他国家心照不宣的默许下,平流层的气溶胶喷雾开始慢慢地止住了气温上升,随后,气温开始下降。
经过多轮谈判,国际社会设定了逐步终止地球工程的最终目标温度。然而,当2099年,最后一架喷洒气溶胶的飞机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市降落时,世界的目光早已转向了其他事情,这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和俄罗斯的争议:正在对高纬度农业造成破坏的人工“云杉树”到底应该由谁负责?这种云杉树是一种早期的人造生物产品,由加拿大的企业推出,用以稳固俄罗斯衰退的北部森林生态系统。
优化人种
2020年,地球工程的第一批实验证实了反对者们(以及有责任感的研究人员们)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那些崇尚科学自由、忽视公共利益的工程师们正是始作俑者,他们拿着石油大享提供的资金,远远地躲开公众视线,在位于南太平洋一座珊瑚岛上的基地中进行了实验。
环保团体已经出离愤怒,他们的抗议使新的研究陷入困境。然而,不管是不是禁忌,地球工程仍是遏制地球迅速变暖的唯一方法。在政府和军队的设施里,研究仍在进行。
尽管如此,气候变化毕竟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人类生殖细胞系改造技术的出现,即在胚胎时期改变孩子的基因组成,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改造生殖细胞系可以提高后代的智力,改善后代的健康和外形,但与此同时,这项技术也在新时代中唤起了人们以往对人种改良的恐惧。到了2050年,这一危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和关注重心。
人类开始分裂成自然人和优化人两个不同的物种。而后者的成员在不同的染色体上有着额外的遗传物质,赋予了他们更高的智力和更健康的身体。亚洲各国广泛接受了新的基因技术。但是由于考虑到少数群体提出的宗教和道德问题,西方国家试图限制人类生殖细胞系改造技术的应用。
气候问题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到了21世纪中叶,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正如科学家们最为担心的那样,气候对二氧化碳的致暖效应非常敏感。2045年,尽管该方面的研究仍然处于遮遮掩掩、零零碎碎的状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还是联手启动了地球工程。也正是在那十年中,美国发生了一次超大旱灾,旱情之严重甚至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旱都相形见绌。
在宗教团体的压力下,美国取缔了遗传操作,国家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缓慢的经济下行期,不安全感和褊狭的思想在美国民众之间滋生。而那场超级大旱把美国推过了爆发的临界点。虽然从来没有确定过干旱是地球工程的意料外后果,但是,对于欣欣向荣的亚洲经济,对于亚洲日益增长的优化人口的强烈愤恨,依然在美国民众中蔓延,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
随着战争的此起彼伏,地球工程的不协调应用变得稀松平常。战争同盟们都试图从对己方有利的角度改变区域气候。天气模式愈加不可预测,区域气候冲突十分常见。在一场战争的激烈对抗中,针对优化人设计的病毒最终被释放了出来,杀死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在这种情况下,对二氧化碳水平上升的担忧早就被遗忘了。
本文作者:戴维·W·基思是哈佛大学教授,安迪·帕克也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通过大型工程改变地球气候,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公共政策。
计算机的未来预言:超越人类?
今天的技术先知对未来之日的看法。
撰文:埃德·雷吉斯(Ed Regis) 翻译:庞玮
预测明年(或下周)的iPad会是什么样就已经够难了,要想知道150年后计算机大概长什么样几乎是不可能的,150年对技术发展而言如永恒般漫长。不过,技术先知、计算机先驱和研究人员在有关未来的问题上向来以大胆奔放著称,所以我们想,问问也没什么坏处。就从这个问题开始吧,在遥远的将来还会有计算机存在吗?
“未来肯定还是有计算机,”牛津大学纳米技术“祭司”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说,“那时的计算机是比汽车轮子还要根本的工具”。
但是以预测为生的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却拒绝预言未来计算机的样子,哪怕推测一下也不干。“也许因为我是个专业的未来学家(futurist),我知道对未来进行精确的预言到头来通常难逃后人的耻笑,所以我尽量与之保持距离。我甚至不喜欢评论别人所做的此类预言,这样做感觉像是在翻看他们的病历,冒犯了他人的隐私,因为你会看到太多的缺点或是幻觉”。
乔治·戴森(George Dyson),曾写过一本有关计算机和全球智慧(global intelligence)的书,他说,“要说起50、100或是150年以前的计算我可以跟你侃侃而谈,但要是谈50、100或150年以后的计算就无可奉告了。真的没法预测,唯一可以保证的是,所有的预言都将是错误的!”不过,他随之就动摇了一下,给出了一个预言,“150年之后绝大多数重要的计算都将是模拟计算(analog computing,基于同样的原因,绝大多数重要的数字都是实数,而非整数),全数字计算(all-digital computation)的概念将成为老古董”。
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是交互式绘图程序Sketchpad的发明人,该程序已成为今天无处不在的图形用户界面的基础,他说:“15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我没任何看法,要想看见未来,去问那些创造它们的年轻人吧。”
“我怀疑年轻人也不知道,”文顿·瑟夫(Vinton Cerf)是萨瑟兰的朋友,身为“互联网之父们”中的一员,他现在在Google工作,他认为:“实际上,那些试图从量子角度降低任何计算所需最低能耗的研究中,可能藏着一些有关未来的启示。另外,我们在人类大脑中见到的那种异步并行(asynchronous parallelism,所谓异步是指计算机的运行不是由单一一个负责时序的中心时钟控制)的运行方式,也许会在‘硬件’中实现,不过我更倾向于相信,未来我们能用更为普通的硬件架构,来实现一些目前难以轻易实现的计算。”
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是庞大的超级并行计算机“连接机”(Connection Machine)的发明人,他说:“我们还会有计算机,但它们也许不再由电子器件构成。这些计算机将更紧密地与我们的意识相连,比今天我们通过屏幕和键盘所形成的联系更为紧密。其中一部分可能直接植入我们的身体,届时人和计算机的分界线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
内森·米尔沃尔德(Nathan Myhrvold)是微软公司前首席技术官,他对这个问题同样持肯定态度,“是的,150年后仍会有计算机,但它们将面目全非。如果你去问爱迪生或是特斯拉今天会不会有电机,他们多半也会回答有,他们猜对了,我们身边每样机械里都有上百个微型电机,偶尔你还会碰到一个能从外形上识别出来的大电机,但绝大多数都已‘溶解’在我们生活之中。150年后的计算机也将如此,我们会看到与今天的计算机相似的机器,但大多数都将隐身于周遭的事物之中”。
“到那时候,计算机的威力将更为巨大,它们将比人类更聪明,如若不然我才真感到吃惊。这会让某些人很不舒服,这些人认为我们理当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东西,但曾几何时,这类人也自信人类的力量是最强大的,但现在在机器面前人类简直不堪一击,我们坦然接受了这一点。今天的计算机在某些狭窄的领域中已经比人要优秀,这些领域会慢慢拓宽,直到计算机全面超越人类”。
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eedman)是微软公司Q工作站(Station Q)的研究人员,Q工作站专注于研究拓扑量子计算(topological quantum computing),弗里德曼则认为,“植入器件不会那么普遍,未来的人体改造会与现在差不多,更注重美丽与外形,而不是计算能力。但是计算器件会变得更小,而且能直接与我们的大脑相连。通过与大脑语言中心的应答,特殊的眼镜或头上的帽子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一门外语”。
弗里德曼接着说,“计算将渗透到环境之中,随着复杂任务(例如通过眼镜翻译外语)所需功耗的降低,不发热的约瑟夫森结逻辑计算机(Josephson logic computers,利用约瑟夫森结代替现有逻辑门制成的计算机)将散布在我们周围。数学的黄金时代将持续繁荣下去,直至人机互动达到难以察觉的完美境界。科幻小说作家担忧那时人类会被机器取代,但150年后的人将能完成更多任务而且做得更好,超过此前任何时代,马拉松世界纪录变成1小时58分59秒,人们不借助绳索也能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巨石山的诺斯线轻易登顶(巨石山是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一座著名的岩石山峰,拥有高达1 000米的垂直岩壁,诺斯线是登上峰顶的一条快速攀爬路线)”。
也许,所有这些预言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违背了计算不可化归性(computational irreducibility)原则,而该原则从认识论上阻碍着我们认识未来。按照史蒂芬·沃尔弗拉姆(Stephen Wolfram,著名数学软件Mathematica的发明者)在他的《一种新科学》(A New Kind of Knowledge)一书中的说法,一个系统被称作计算不可化归的,是指该系统“在实效上,无法通过比该系统自身演化更少的计算步数,来预测该系统未来的行为”。换句话说,“没有捷径,你得把所有杯子都翻开,才能知道哪些杯子下面藏了乒乓球”。
通向未来计算机的技术之路似乎就构成了一个不可化归系统,它将集万众于一体,其中包括无数人类的判断、技术创新、市场驱动和消费者的选择,看上去没有任何方法能预先知晓,这些力量和判断将会以何种方式在相互应答之间塑造出技术的未来,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知道未来的计算机究竟样貌如何,而只能静待150年的时光流逝,让后人一探究竟。
本文作者:埃德·雷吉斯名下有8本著作,最近的一本是与乔治·M·丘奇合作完成的《再生:合成生物学将如何重塑自然及我们自己》。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