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西兰库克海峡(Cook Strait)一角的北兄弟岛(North Brother Island)上,一群类似蜥蜴的生物——楔齿蜥(tuatara)的雌性个体正在消失。20世纪90年代末,当科学家们首次注意到楔齿蜥的性别比例失衡时,雄性已经占到62.4%。从那时起,情况不断恶化,目前的雄性比例已经超过70%。研究人员称,该物种性别比例失衡的诱因是气候变化:地表温度决定了楔齿蜥的性别比例:较低的温度有利于产生雌性个体,而较高的温度有利于出现雄性胚胎。当雄性比例达到85%时,北兄弟岛的楔齿蜥将会不可避免地跌入生物学家所称的“灭绝漩涡”(extinction vortex)中。
对于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楔齿蜥以及许多其他物种来讲,将它们迁移到之前从未生活过的地方——即“辅助迁移”(assisted colonization),似乎开始成为动物保护者拯救物种的唯一选择。明尼苏达大学的生态学家、首次提出“辅助迁移”思想的研究者之一杰茜卡·赫尔曼(Jessica Hellman)说:“我们倾向于采用更自然的方法。”也就是说,当原有的栖息环境已不再适合生存,最理想的情况是,这些物种可以主动迁移,利用自然廊道寻找新的栖息地。但是对于很多生活在岛屿和山林中的物种来说,长距离迁移绝对不是首选。此外,在很多地方,原有的生态走廊因为人类的发展而遭到破坏。
然而,将辅助迁移用作保护策略的想法却遭到激烈的批评,批评者质疑辅助迁移可能会给迁移的物种和目标栖息地带来生态浩劫。此外,很多动物保护者毕生致力于将物种放归到它们一两百年前生活的地方——如将狼放归黄石公园、将野牛放归大平原(Great Plains)。在他们看来,让这些动物生活在全新的环境中简直不可接受。
但是,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灾难已经显而易见,批评和反对的声因暂时让步,因为对辅助迁移的时间、实施方式进行规划已经迫在眉睫。如有必要,还需提高大众对辅助迁移的接受度。最近,在《Elementa:人类世科学》(Elementa:Science of the Anthropocen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超过2300名生物多样性研究人员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有条件地支持辅助迁移,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方法能够阻止物种灭绝,并且目标栖息地承受的风险可以控制到最低。
逃离栖息地
去年11月的一场灾难中,人们意识到物种应急疏散预案的重要性。在西澳大利亚州的干旱地带,一场山火摧毁了世界上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 ——吉尔伯特长鼻袋鼠(Gilbert's potoroo,一种类似袋鼠的小型有袋动物)的栖息地。在保护区内的约20只长鼻袋鼠中,有15只在这场火灾中丧命。该物种在一个多世纪前曾被认为已经灭绝,后于1994年在该保护区被重新发现。如果不是动物保护者在长鼻袋鼠重新出现后,将部分个体迁至保护区附近的一片区域,从而形成一个单独的种群,在这片栖息地毁于大火时,该物种可能已经被宣判了死刑。
长鼻袋鼠的迁移是在原有栖息地范围内进行的,相比于迁移到一个全新的区域内,争议较少。其他地方的动物保护者也已经开始效仿此举,为物种争取生存的时间。比如,在佛罗里达群岛,由于海平面上升,研究者已经把礁鹿(key deer)以及树枝状的仙人掌转移到高处,以期它们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因为海平面上升而失去栖息地。对小型啮齿类动物——珊瑚裸尾鼠(Bramble Cay melomys)而言,这种缓兵之计却已为时已晚。今年六月,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由于岛屿栖息地遭到洪水反复侵蚀,该物种已经灭绝。他们认为这是“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第一例哺乳动物灭绝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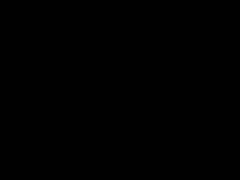
因此,延续其他物种生命的最大希望,可能存在于原有生存范围之外的区域。比如,澳大利亚的极危物种澳州短颈龟(western swamp tortoise)生活在珀斯周边的沼泽地区,那里面临着来自气候变化、城市扩张以及城市地下水位下降的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其他地区的三倍。昆士兰大学的特雷西·劳特(Tracy Rout)和同事应用超级计算机对该地区附近13 000个可能的迁移位点进行了分析。对地面的进一步研究已经将可能的迁移位点列表缩至城市以南几小时车程处的几个地方。在今后30到50年内,气候会更加干旱,但这些地方的水文特征以及其他条件依然适合短颈龟生存。在获得野生动物和环境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研究者们于今年8月将圈养环境中的短颈龟运送至它们在珀斯以南的新家。
其他研究人员正在为澳大利亚极危物种山袋貂(mountain pygmy possum)的迁移地点争论不休。这需要对迁移过程的复杂程度进行估计,因为它们偏好的食物——布冈夜蛾(Bogong moth)可能也需要随之迁移。这两个物种所生活的高山环境正在迅速升温,仅仅将其移至海拔更高的地方已经于事无补了。
应用辅助迁移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全新的手段。英国杜伦大学的生态学家斯蒂芬·G·威利斯(Stephen G. Willis)和现任职于约克大学的哈内·K·希尔(Jane K. Hill)在1999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尝试。“我们过去一直在研究气候变化对英国蝴蝶的影响,包括相对常见的大理石条纹粉蝶(marbled white)、有斑豹弄蝶(small skipper)等,” 希尔说,“在这些蝴蝶正常活动范围以北它们还未涉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些气候适宜的区域。”
这些区域至今未有这些蝴蝶生活的原因是“迁移滞后”(migration lag)现象,即使生态廊道完好无损,但物种迁移的速度往往慢于气候变化的速度。对树木而言,这种滞后现象是可以预期的。但研究表明,滞后现象同样发生在鸟类和许多哺乳动物身上,这或许是因为这些物种依赖于变化缓慢的植被和栖息地类型。“气候速度”与“生物速度”之间的差距是难以逾越的。比如,华盛顿大学的乔舒亚·J·劳勒(Joshua J. Lawler)预计,由于黄条丛蛙(yellow-banded poison dart frog)所生活的雨林环境正变得愈加干燥、炎热,它们需要在本世纪向西南方向跳跃数百千米才能找到适宜的栖息地。
当威利斯和希尔注意到大理石条纹粉蝶和有斑豹弄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滞后现象时,他们开始帮助这些蝴蝶追赶气候变化的脚步。希尔说:“我们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一个示范,一个好的案例研究。” 威利斯和希尔能够获得批准,是因为他们所提议的迁移位点相对局限在采石场以及市区,人们已经知道那里的物种是可以与这些蝴蝶共处的。他们在大理石条纹粉蝶原始生活范围以北65千米处和有斑豹弄蝶原始生活范围以北35千米处分别释放了这两种蝴蝶。威利斯介绍说,这两种蝴蝶在新家的生活状况很好。但是,辅助迁移的指导方针“是保证不能出错,我们必须谨慎行事,采取保守的策略。因为你不希望再往澳大利亚引进一批兔子(兔子曾是澳大利亚入侵物种)。”
谨慎决策
任何物种的迁移都存在着风险。在2009年的一篇评论文章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安东尼·里恰尔迪(Anthony Ricciardi)和美国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的丹尼尔·辛贝洛夫(Daniel Simberloff)要求动物保护者切莫上演“生态轮盘赌”的游戏,并警告那些辅助迁移的支持者,即使他们再怎么谨小慎微,也可能已经“极大地低估”了预测引进物种对栖息地影响的难度。
这两名作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出于为松貂(pine marten)提供食物来源的考虑,纽芬兰政府决定将松鼠(red squirrel)引进黑云杉(black spruce)森林。可是随后,松貂的数量开始下降,并且对松鼠也不感兴趣了。在9000年的演化历程中,黑云杉森林中从来没有松鼠生存过,因此无法抵抗这个外来物种的威胁。纽芬兰的红交嘴雀(red crossbill)依存于黑云杉森林,它们在与松鼠的竞争中也严重受挫。红交嘴雀已被列为濒危物种,并成为一个被拿来研究的案例:当人们把物种迁出历史生活范围后,善意也会造成严重的错误。

然而,我们可能有办法把灾难性后果出现的几率降至最低。2013年,伦敦动物学会的纳萨利·佩托雷利(Nathalie Pettorelli)和同事就开始对新西兰的缝叶吸蜜鸟(hihi)进行研究。这种鸟羽毛呈黄黑色,可以在空中悬停。这种经过了3400万年演化的鸟类仅生存于新西兰北岛及附近的5处孤立的栖息地中,那里的动物保护者为它们提供了北美的蜂鸟常用的喂食器。佩托雷利与合作者发现,未来数十年的气候变化将使得该地区很大程度上不再适合该鸟生存。然而,缝叶吸蜜鸟历史生活范围之外的新西兰南岛却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形成了适合该物种生存的环境。
佩托雷利说:“我们并不是想去讨论在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向何处迁移缝叶吸蜜鸟。”这是当地管理者的工作。但是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细致的决策方式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方法上的指导。他们首先剖析了迁移存在的五种风险——对其他物种的负面影响(生态风险)、新病原体的引入(疾病风险)、可能向目标范围以外扩张,并在与本土物种的竞争中胜出(入侵风险)、与近缘物种杂交(基因漂移风险)和居民成本(社会经济风险)。为了使模拟尽可能准确,他们还考虑到了新旧栖息地的许多气候因素,比如旱季的干旱程度、降水量的周年变化等。
“我们需要增加决策人员和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许多人希望进行合作,但却不知道该如何实现,他们之间缺少桥梁,” 佩托雷利说,即使是现在,“还有许多管理决策没有基于科学知识,没有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科学。” 佩托雷利等人的工作向人们展示了应该如何开展合作。目前,动物保护者已经在北岛新建了一个缝叶吸蜜鸟种群。
不确定的结果
即使是辅助迁移的支持者,现在也开始担心他们可能有些操之过急了。有时候顺其自然的选择——让物种自身主动调整适应——也可能没那么难。比如,在丹佛西部的落基山脉,随着温度上升,高山花卉的数量下降。因此,那里专门吸食拥有较深花冠管的花朵的熊蜂(bumblebee)也不那么挑剔了。演化方向也因此逆转:熊蜂的舌头在过去40年间缩短了1/4。
物种同样可能具备科学家想象不到的适应能力。2010年,研究龙虾商业捕捞的科学家从澳大利亚南部的深水区迁出了一万只红岩龙虾(southern rock lobster)。然而,研究人员并没有将红岩龙虾向极地迁移、在寒冷水域建立前哨种群。相反,为了观察红岩龙虾如何应对未来较暖的环境,研究人员将它们迁移到了靠近赤道的近岸区。与我们的直觉相反,这些红岩龙虾的生长速度是原来的4倍,每年的产卵量也增加了35 000枚。在食物丰富的温暖环境中,红岩龙虾比研究人员预想的更加适应温度的变化。

对物种适应能力的预测极具挑战性。最近,研究人员分析了155种生活在英国的蝴蝶和蛾在过去40年气候变化中的遭遇,研究发现:一半的物种情况在变好,而另一半变得更糟。物种不同,可能的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夏季气温、冬季气温、春季降水量等对不同物种造成的影响也不同。英国约克大学的克里斯·D·托马斯(Chris D. Thomas)说:“结果就是,这155种蝴蝶和蛾对气候的变化程度、气候是在好转还是恶化等问题几乎有155种不同的‘看法’。”

那么,这些不确定性会让楔齿蜥这样的物种何去何从呢?雄性楔齿蜥每年都能交配,然而北兄弟岛上的雌性楔齿蜥每9年才能繁育一批后代。这意味着,雌性楔齿蜥会不断受到雄性的交配骚扰,这会迅速损害它们的健康。而随着楔齿蜥性别比例严重失衡,这个问题正在恶化。北兄弟岛没有荫蔽、墙角或者石缝这些温度比较低的地方,不能减少温度升高造成的性别失衡。那里的约500只楔齿蜥已经成为风向标,告诉人们气候变暖将如何影响整个物种。目前,北岛和南岛上的楔齿蜥已经被转移到若干小岛上,这些仅存的10万只楔齿蜥是该物种2亿年演化历程中最后的幸存者。

西澳大学的尼古拉·米切尔(Nicola Mitchell)最近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列出了北兄弟岛的各种管理措施。所有关注楔齿蜥的力量——从科学家、政府管理者到毛利人(楔齿蜥是毛利人的图腾)可以联合起来清除不需要的建筑,在岛屿上温度较低的地带建立筑巢位点,或是由研究人员寻找楔齿蜥的蛋,并利用人工孵化器达到适当的温度,从而使性别比例均衡。研究人员还可以保护刚孵化出的雌性幼体,将它们放归到种群中时移除过剩的雄性个体,从而重建性别平衡。

米切尔说:“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难度都很大。”米切尔曾花费两个夏天在岛上寻找楔齿蜥的巢穴。“每年雌性巢穴数量都非常少,并且很隐蔽,很难发现。”将楔齿蜥转移到温度较低的地带可能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花费较大:每次都需要从惠灵顿市区乘直升机飞往北兄弟岛,这是一项很大的开支。目前,最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北兄弟岛种群作为一个试验品。科学家们可能只是想等着看该种群自身会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果北兄弟岛的楔齿蜥种群灭绝了,那就顺其自然吧。

最终,这些决定都将归结为保护生物学家和整个社会对于人为干涉自然的态度,毕竟这涉及到保护哪些物种,而哪些物种只能走向灭绝。明尼苏达大学的赫尔曼发问:“什么时候算是与自然进程合作,什么时候只能算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保护物种?毕竟,人类不可能保护所有的生物多样性。”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