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布赖恩·巴特沃思一直致力于了解一种名为“计算障碍”的识数能力缺陷疾病,
并试图帮助那些不幸患有此病的人。
撰文:尤恩·卡拉韦(Ewen Callaway) 翻译:郭凯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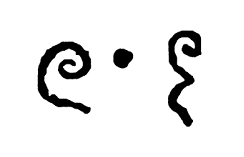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拍摄一部关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五周年的纪录片,身为战地记者的保尔·莫尔克拉夫特(Paul Moorcraft)跟着一个电影摄制组进入阿富汗境内,来到了苏军战线的后方。“我们每天都受到俄罗斯人攻击,”莫尔克拉夫特回忆说。不过,真正麻烦的事还在后面——当他想要算一下总的花费时(例如为摄制组购买马匹和当地衣服所花的钱),哪怕是使用计算器,做这样简单的加法,也花了他比通常多十倍的时间。“这绝对是一场噩梦,我把整天整天的时间都用在这件事上”。当他最后总算把账单寄给会计师时,他没有意识到,他在总额后面多加了一个零,结果这趟本来花费几十万英镑的旅程,他却报出了几百万英镑的开销!“会计师知道我是个本分的人,因此认为这只是打字疏忽闹出的笑话而已”。
如今,莫尔克拉夫特已是英国外交政策分析中心主任,出过十几本大作,然而上述失误却始终跟随着他。多年来,他的电话号码与PIN号从未变过,因为他担心一旦改变,自已可能会永远也记不住新号码。在英国国防部工作时,他把记住安全代码的任务交给了下属。2003年,由于弄错一个电话号码,他遭到了沉重打击——尽管以前他曾弄错过数百个号码,但这次出错却使他失去了女友,因为后者坚信,他当时正外出跟别的美眉厮混。这次打击终于使他下定决心,要弄清楚为何这些简单的数字总跟自己过不去。
他有一位教育学习障碍儿童的朋友,在这位朋友的建议下,他联系了在伦敦大学学院研究数字认知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布赖恩·巴特沃思(Brian Butterworth)。进行了一些测试后,巴特沃思认为莫尔克拉夫特的算术“简直一塌糊涂”,并诊断他患有计算障碍。这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学习障碍,有时被称为“数盲症”,与数学读写困难有关。研究人员估计,患有计算障碍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7%,这种学习障碍的特点是,患者在处理数字时会遇到严重困难,尽管其他方面的智力完全正常(甚至可能远高于常人,莫尔克拉夫特就是如此)。
这种奇怪的病症引起了巴特沃思等神经科学家的注意,他们相信,对计算障碍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大脑“数觉”功能(即认识和处理数量的能力)的运作机制。数觉与视觉、听觉一样,完全是天生的,但对于它的认知和神经基础,科学家存在不同看法,对计算障碍的研究或许会有助于摆平这方面的争论。
对巴特沃思而言,科学上的好奇心最终转化为他对与计算障碍相关的宣传教育活动的全心投入。“我认为,仅仅找出它的原因是不够的。”过去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让家长、教师、政治家及一切愿意听他解释的人,了解并认识这种疾病。此外,他也运用自己对这种疾病的了解,来帮助那些患有计算障碍症的儿童。“如果你只是告诉某人患有计算障碍症却又爱莫能助,那又有多大用处呢?”他说。
数字怎么了
克里斯托弗(化名)是一个爱说话的9岁男孩,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蓝色毛衣和一件保罗衫,坐在老师帕特里夏·巴布蒂(Patricia Babtie)旁边(巴布蒂的专业就是研究计算障碍症,负责辅导大伦敦地区的患儿)。眼下克里斯托弗正在一台看来很牢实的笔记本电脑上玩“数觉”游戏,这是巴特沃思和他在伦敦教育研究所的同事黛安娜·劳利拉德(Diana Laurillard)合作设计的一套教学用电脑游戏。
关于计算能力的认知,目前存在若干互相对立的理论,巴特沃思希望通过研究计算障碍症的治疗方法来检验这些理论。如果计算障碍症本质上是缺乏基本数觉(这正是他的看法),而非其他学者所认为的是缺乏记忆、注意力或语言能力,那么,设法培养数觉就应该对计算障碍症患者有所帮助。“这些孩子需要的,只是比其他人多做这方面的练习,”巴特沃思认为。伦敦已有几所学校正在使用上述游戏软件,克利斯托弗所在的学校便是其中之一,古巴、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学生,也将很快开始使用这个软件。
克里斯托弗一开始玩的游戏同数轴有关(数轴是数的一种空间表示法,科学家认为,它对数觉起着关键作用)。“200与800之间正中的数字是哪一个?你知道吗?”巴布蒂问。克里斯托弗耸耸肩。“随便想一个比200大、比800小的数,把它填在这个框里。比如可以是201,”她说。克里斯托弗填入了200,巴布蒂提醒他填入的数必须比200大。于是他选了210(说不定是把它当成201了)。巴布蒂认为,计算障碍症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难于掌握整数数位系统。“这个填得不错,”她说。而电脑则发出一个柔和的声音,要克里斯托弗“找到并点击那个数”。这个游戏就是反复地缩放数轴,每做一步克里斯托弗都要加以详细解释(巴布蒂鼓励他这样做),不过他足足花了一分多钟才找到210。而他的同班同学已经在学习两位数的乘法了。
在克里斯托弗所在的学校,某些学生识数问题更加严重。一位9岁的同学说,她不知道50大于还是小于100,另一位9岁同学则把4个点数成了5个,而且在做数字较小的加法时还得靠数手指头(这是计算障碍症患者常用的方法)。
“好啦,今天就到这里。改天我们还得做更多练习,”巴布蒂对克里斯托弗说。这20分钟真让她够受的。看得出来,克里斯托弗宁愿回到班上,也不愿呆在这间屋子里,学他的同学几年前就已经学会的这些数学知识。
数觉认知根源
现年69岁的巴特沃思既是学者,也是公众人物。他是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士。对口吃与语言障碍所作的研究使他声名大振,多年来频频现身于英国媒体。例如,1984年,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巴特沃思声称,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讲话习惯表明他患了阿尔茨海默症。10年后,里根真的被确诊患上此病。
20世纪80年代后期,巴特沃思曾研究过一位中风病人,正是这位病人改变了他的职业方向。这位59岁的女性病人来自意大利,曾是一名酒店主管,她的语言智商测试达到一般水平,记忆力相当不错。但是,当巴特沃思的意大利同事请她数数时,她会开始数“uno, due, tre, quattro”(1、2、3、4),然后就停下来。“Miei matematica finisce alle quattro”(我只能数到4了)——这位被称为CG的女士总是这样告诉大家。
大约在20世纪初,神经病学家就介绍过对CG这类“失算”(acalculic)患者的一些病例研究,不过“人们对于计算所涉及的具体大脑部位并未有太多考虑,”巴特沃思指出。对CG的脑扫描显示,她的顶叶——位于耳部正上方的大脑区域——存在一处病变。后来,巴特沃思发现另一位病情正好与CG相反的患者:这位患者的神经退行性变已经使他丧失了讲话和语言能力,也忘掉了很大一部分知识,但却没有影响他进行复杂计算的能力。于是巴特沃思越发肯定,人的识数能力由专门的大脑神经网络控制,而不是如许多科学家当时所认为的,由实现一般智力功能的神经网络控制。
巴特沃思提出,遗传因素以及大脑发育异常破坏了计算障碍症患者的这些神经网络。莫尔克拉夫特给巴特沃思提供了很多启示,因为他在不同领域中的能力存在巨大反差。巴特沃思及其同事还测试了31名8至9岁的儿童,这些儿童的数学成绩在各自班上基本垫底,但在其他科目上却表现得足够给力。与正常儿童及患有读写困难症的儿童相比,患有计算障碍症的儿童对几乎所有的数字问题都感到头疼,异常吃力,但在阅读理解、记忆力及智商的测验中则达到平均水平。
对于巴特沃思来说,这项研究证实了计算障碍症是由于病人在数字理解上存在根本问题导致的,而不是其他认知功能存在问题。但要弄清楚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则极具挑战性。
同几乎所有的人类认知功能一样,“数觉”的进化历程也非常古老,即使没有数亿年,也总有几千万年了。对黑猩猩、猴子、雏鸡、蝾螈乃至蜜蜂所作的研究都表明,存在着两种并行的表示数量的系统。其中一种称为“近似数觉”,它只区分数量的多少,无论是屏幕上闪现的点还是树上的水果。对猴子的研究揭示,当猴子看到越来越大的数量时,顶叶一个特定褶皱中的某些神经元活动就会变得更加强烈。而第二种古老的数字系统则让人和其他一些动物能够立即准确地识别出较小的数(4及以下)。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证明,在那个名叫“顶内沟”的褶皱内,各个神经元似乎对应于不同的特定数量——比如,当一只猴子在完成一项与数字有关的任务时,某个神经元的活动对应于数字l,而另一个神经元的活动则对应数字2,如此等等。
不善于识别近似数的人数学方面的表现很差,这种关系意味着近似数系统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有些研究证明,计算障碍症患者难于识别较小的数,这提示识别较小数字的能力对于数字处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此外,对计算障碍症患者的脑扫描显示,与识数能力正常的儿童及成人相比,他们的顶内沟在处理数字时活跃性较低,与大脑其余部分的联系也比较弱。
不过,巴特沃思认为,这些情况是计算障碍症特有的数字能力低下所带来的后果,而不是原因。他指出,另一种认知能力对数觉更重要。他把这种能力称为“数量编码”,也就是认识到,所有东西均有一个确切的数量,拿走或拿来可以改变数量。
然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所(INSERM)研究数字认知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斯坦尼斯拉斯·德哈尼(Stanislas Dehaene)认为,数觉是由更广泛的一组认知功能支持的。他指出,尽管识别近似数和较小数字的能力很重要,但对于准确理解较大的数字却还不够。他认为,语言使人能把两个数字系统整合起来,从而赋予他们直观区分像11 437与11 436这种数字的能力。德哈尼宣称,巴特沃思关于数量编码的概念或许是数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个概念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地方,比如,它是否存在于其他动物中,是否很早就存在于儿童中,等等。
有一篇题为《6不代表“多”的意思:学龄前儿童眼中的数字就是指特定的数量》的论文,巴特沃思最为欣赏。在这篇论文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发展心理学家芭芭拉·萨尼卡(Barbara Sarnecka)和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的苏珊·格尔曼(Susan Gelman)证明,幼儿还不知道数2,却已经知道向一只已经有6枚硬币的碗中加入硬币会改变数量,尽管他说不清楚究竟是怎样改变的。如果数量编码是一项根本性的能力,那么可以预测,像莫尔克拉夫特或克里斯托弗这样的计算障碍症患者,在处理所有大大小小的数字时都会非常吃力。巴特沃思希望数觉游戏可以锻炼患者的这项能力,从而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
经过3个月的练习,克里斯托弗的数轴游戏似乎玩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他进展非常快,以至于巴布蒂要求他慢一点,解释一下每一步的理由。巴布蒂说,当患计算障碍症的儿童详细解释他们的操作时,学习进度通常就会大大加快。她相信克里斯托弗的数学焦虑症(这是患计算障碍症的儿童与成人普遍存在的一种状态)正在逐步消失。
随后,克里斯托弗又转到另一种名为《数字键合》(Numberbonds)的游戏上。这个游戏与俄罗斯方块相似:各种长短不等的条块从屏幕往下落,克里斯托弗必须选择长短合适的方块来填满一行。这个游戏的重点在于弄清空间关系,但部分计算障碍症患者对于空间关系也极为头疼。刚开始时,方块移动得太快,克里斯托弗非常恼火,但不多久他就掌握了这个游戏的诀窍。当巴布蒂告诉他今天就到此为止时,他还恳求巴布蒂再让他玩十分钟。
在巴特沃思看来,数觉游戏——包括一款看起来非常时髦的iPhone版Numberbonds游戏——主要是用来培养数字认知的基本能力,以及计算障碍症患者缺失的核心能力,即处理确切的数量。比如,一款名叫《追踪点》(Dots to Track)的游戏要求儿童为点阵图(即由类似于骰子上的点构成的图案)分配一个阿拉伯数字。如果他们填入的数有错——他们出错可谓家常便饭,那么游戏会要求他们添加或去掉一些点以得到正确的答案。
暑假来临时,巴布蒂担心克里斯托弗以及其他学生不会在家里继续练习这些游戏,秋季返校时,他们的成绩可能会回落。然而10月初开学时,克里斯托弗宣称他将挑战一个从950延伸到9000的数轴游戏,“如果你同意的话,”他补充道。刚开始他有点手足无措,但很快就熟悉了这个游戏,找到了一连串的4位数字。每答对一次他就眉开眼笑,兴奋至极。
不知是什么原因,其他学生的进步要慢一些。巴布蒂指出,读写困难、注意力缺陷障碍以及自闭症谱系疾病等,在计算障碍症患者中非常普遍,要弄清这些疾病之间的关系相当困难。那位9个月前还在靠手指头数数的9岁男孩,现在可以应付6以下的数字了,但区分9与10对他来说仍然十分费劲。不过巴布蒂认为,只要坚持进行正确的练习,教师和家长给予充分注意,患计算障碍症的儿童是可以正常成长的(她强调说电脑游戏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不能取代一对一的教学方式)。
巴特沃思很清楚,只有在对数觉游戏进行对照评估之后,他才能判断数觉游戏是否真的有助于提高患儿的识数能力。而对其他电脑化干预手段作的小规模比对研究显示,这些游戏是有帮助的。2009年德哈尼称,通过使用他的团队开发的游戏《数字赛跑》(Number Race),15名患计算障碍症的学前班儿童识别两个数中较大一个的能力有了一定提高,但对算术和计数能力则没有起作用。与此同时,瑞士的一个研究团队在2011年称,一款让学生把宇宙飞船放在数轴上的游戏,有助于提高8到10岁患者的算术水平。研究人员安排学生完成一项涉及数字排列的任务,同时对学生进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他们发现,训练后一个月,儿童顶内沟的活跃程度有所增强,而顶叶其他区域的神经元活动则有所减弱。这表明,算术能力的进步,与大脑中负责对数字作出应答区域的变化有关。
巴特沃思希望能在克里斯托弗这样的学生玩数觉游戏时,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以观察他们的顶叶是否发生了变化。为此他多方申请经费,却全都空手而归。尽管计算障碍症像其他各种学习障碍一样,对生产效率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一项报告估计,识数能力欠缺给英国带来的损失高达每年24亿英镑(40亿美元),主要是工资的损失〕,但它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对这种疾病的研究也就拉不到多少赞助经费。比如2000到2001年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出了200万美元来研究计算障碍,但同期用在读写困难上的研究经费则超过1.07亿美元。
巴特沃思的团队现在已经有了初步计划,打算明年与古巴神经科学中心及哈瓦那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评估他们开发的软件。团队还把这款游戏软件投放到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新加坡。“说来也怪,古巴人乐于花钱做这项研究,虽然他们拥有的经费并不多,”巴特沃思表示,自己很欣赏古巴的教育体制。
虽然巴特沃思只是一位名誉教授,严格地说已经退休,但他仍在发挥余热,研究数觉的神经发育根源。不久前,他还证明了虹鳉同人一样,拥有“近似”与“准确”两种数字系统。他还证明了,患计算障碍症的成年人与识数能力正常的人一样,可以看懂钟表。
巴特沃思希望,如果增强数觉真的能够改善计算障碍症的病情,那将有助自己在有关识数能力认知基础的论战中取胜。而德哈尼则没有对电脑游戏寄予太多希望。德哈尼或许是巴特沃思在这场论战中最强劲的对手,他的《数字赛跑》游戏及后继版《数字捕手》(Number Catcher)整合了多种数字技能,即使这个游戏能起作用,也不能解决哪些技能对数觉最重要,哪些技能在患者中受损最严重等问题。“我很快就意识到,儿童只是对充满创意、有趣的娱乐游戏感兴趣,这同科学分析的路线是格格不入的,”德哈尼说。
巴特沃思也说,归根到底他的动机主要是想帮助有计算障碍的儿童。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点使他感触颇深:“数学差对孩子们的打击非常非常大。孩子们每天都得上学,每天都有数学课,因此每天都会感到难堪——我的数学不行,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好。”
莫尔克拉夫特对那些孩子也颇为同情。遇到患计算障碍症的儿童时,他会告诉他们,自己也会悄悄地靠手指头来数数,并开导他们这没什么可难堪的,只要勤加练习(他那时连练习的机会都没有),一样可以赶上别人。
莫尔克拉夫特同巴特沃思的一位博士后研究生合作,完成了一部有关计算障碍症的著作,这本书即将完稿。“我已经写好了序言,”他自我解嘲地说,“只希望各章节的顺序不要搞错。”
本文作者:尤恩·卡拉韦是《自然》杂志驻伦敦的撰稿人。
请 登录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