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搜索改变大脑
撰文 丹尼尔 · M · 韦格纳(Daniel M.Wegner)
阿德里安 · F · 沃德(Adrian F.Ward)
翻译 邹璐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将大脑的工作分摊给他人。每当面对新的信息,我们只会记住其中的某些东西,而自动将记忆其他事实与概念的任务,分摊给群体的其他成员。当我们记不起某人的名字,或者不知该如何修理一台坏掉的机器时,只要向负责记忆这些信息的人求助就好。如果你的车开始咣当乱响,你会给“好机友”雷伊(Ray)打电话。记不得《卡萨布兰卡》的主演是谁?问问电影控玛西 (Marcie)就行。任何社会单位——不论一对夫妇,还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会计部门,都会将记忆人、事、物的琐细任务分派到不同成员的头上。在上述几个事例里,我们不仅知道自己脑海中储存的信息,也“知道”其他同伴负责记忆的信息。
这种分配模式避免了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还能扩大一个群体的记忆总容量。当我们将记忆某类信息的任务托付于他人,自己原本负责这部分记忆的认知资源就得到了解放。作为交换,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加深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比起各自为战,群体成员对信息负荷的相互分担,使得每一个个体都能获得更广泛、更深入的知识。记忆的分配将一个群体维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从整个群体的“知识库”中提取信息,那么任何一个个体都不算完整。一旦相互分开,那对奔赴生日宴会的夫妇肯定会傻眼,一个人可能不得不穿着燕尾服在街头游荡,另一人虽然可能准时到达宴会,身上却套着运动衫。
有赖于所谓的“交互记忆系统”,这种分担信息的趋势,在一个“面对面互动”的世界里发展起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类大脑代表了信息储存能力的巅峰。然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曾经“火力全开”的人类大脑已在竞争中落败。
iPhone的Siri进入社交群体后,一切发生了改变。当今世界,几乎所有信息都能通过互联网搜索得到。我们的研究认为,人类已差不多将互联网,当作了交互记忆系统中的人类伙伴。我们像拜托家人、朋友、爱人时一样,将记忆交给了“云”。然而,互联网却不同于人类交互记忆系统中的拍档——它知道得更多,制造信息的速度更快。互联网不仅可能取代了“他人”这种外援式的记忆资源,也取代了我们本身的认知官能。互联网不仅消除了我们与同伴分享信息的需要,也瓦解了将即时习得的重要信息,存储进生物式记忆系统的冲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谷歌效应”(Google eff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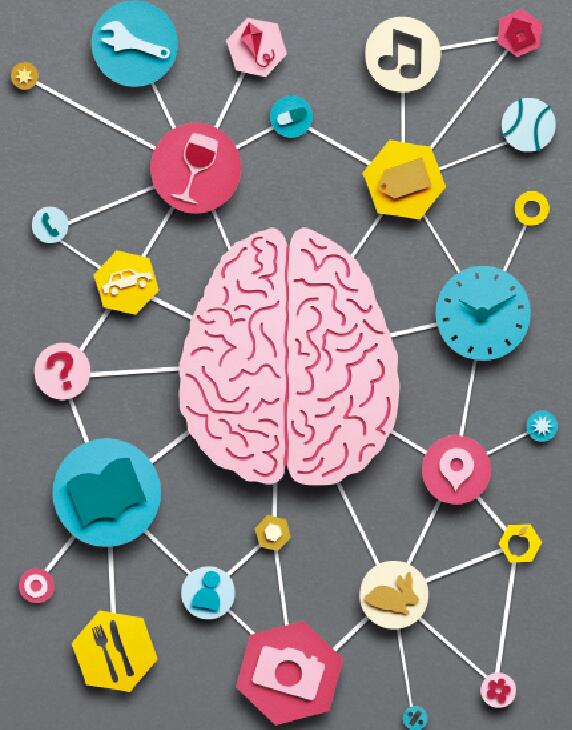
新的记忆拍档
我们最近的一项实验,显示了互联网已在多大程度上将朋友或家人取代,分担我们的日常记忆任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贝其· 斯帕罗(Betsy Sparrow)、当时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珍妮·刘(Jenny Liu)和本文作者之一韦格纳,让受试者将40个好记的简单事实(例如“鸵鸟的眼睛比脑大”)输入电脑。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被告知电脑会储存他们的工作,而另外一组则以为这些句子将被删除。此外,不论电脑是否会储存信息,每一组都有半数的成员被要求记住这些句子。
我们发现,那些相信电脑已经保存了信息的受试者,记忆句子的效果更差一些。他们似乎把电脑当做了我们几十年前就开始研究的“交互记忆拍档”,习惯性地将信息交付电脑,而非自己的大脑。令人惊讶的是,即便研究人员明确要求受试者记住相关信息,这种趋势也依然存在。似乎,只要有“网络伙伴”在,人们将记忆负荷交给数字设备的愿望就会无比强烈,以至于无法将细微的事情“刻进”脑海。
我们的另一项实验,是研究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求助于互联网的快慢程度。为探索这个问题,我们采用了心理学家称为“斯特鲁普任务”(Stroop task)的方法,让受试者查看一系列颜色不同的单词,并在忽略单词意思的前提下,识别单词本身显示的物理颜色。通过测量受试者的反应速度,我们可以判断每个单词吸引受试者注意力的程度。如果他们对某个单词的反应较慢,我们就可以假设,这个单词的含义与他们正在思考的东西有关。比如,一个24小时没有进食的人,认出一个代表食物意思的单词的颜色的速度,就比一个已经吃饱的人更慢一些。与食物有关的单词,和受试者当前的需求息息相关,所以他很难忽略这些单词的意思,作出反应的时间也就更长。
在我们的实验里,受试者需要完成两项斯特鲁普任务:一个任务在回答简单的细节问题后进行,另一个则在回答困难的细节问题后进行。斯特鲁普任务里的单词,要么与互联网相关,比如红色的“谷歌”(Google),或蓝色的“雅虎”(Yahoo);要么就是普通的品牌名称,比如黄色的“耐克”(Nike)或绿色的“塔吉特”(Target)。
我们发现,回答困难的细节问题——即受试者无法独立回答的问题(比如“是否每个国家的国旗都至少有两种颜色?”),对他们之后识别颜色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的影响。与一般的品牌单词相比,人们在识别与互联网相关的单词的颜色时,花费的时间更长。这表明,当我们遇到无法回答的问题,“上网”的冲动,会很快进入我们的脑海。显然,当有人要求我们提供自己不知道的信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互联网”这个无所不知的“朋友”。只需手指简单地一点,或者发一条毫不费力的语音指令,它就能告诉你想要的信息。将记忆多种信息的任务转交给互联网,或许意味着我们已经用无所不知的数字云端,替换了交互记忆系统的其他拍档——朋友、家人,还有其他人类专家。
新的自我
从朋友和熟人组成的交互性社会网络,到数字化的云端,我们分派记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符合常理。散落于互联网的海量字节,与储存在一个朋友大脑中的信息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互联网将信息储存起来,并能根据问题,从中检索答案;它甚至还能以出人意料的人性化方式与我们互动——使用过Siri的人一定知道这样的感受。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不同于我们之前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因为它总是存在,永远处于“开启”状态,几乎无所不知。智能手机能够获取的信息,远多于任何一个人所能记忆的信息,很多时候甚至大于一整个群体所存储的信息量。它总是在更新,除非“断电”,它绝不会记错或忘记,而我们的大脑却经常出现这些问题。
互联网的惊人效率,与传统的信息搜索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若要向朋友咨询问题,我们一般需要先知道他们的行踪,并在心里祈求他们知道我们想要的东西,还要等他们磨磨蹭蹭地一边清嗓子,一边在头脑里搜寻答案。同样,如果想查询书中的信息,你需要先开车到图书馆,然后在分类卡片里慢慢摸索,接着在书架间来回穿梭,然后才能找到想要的材料。我们向熟人或参考书寻求信息的行为,恰恰强调了我们对外部信息资源的依赖。
然而,谷歌和维基百科改变了这一切。当我们的密友变作互联网,个人的内部记忆(存储在大脑里)和外部记忆(从前是朋友,现在是互联网)的区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智能手机从互联网提取信息的速度,有时比我们从自己记忆中提取信息还要快。智能手机搜索信息的即时性,或许已开始模糊个体记忆与互联网上大量数字信息间的界限。
最近,我们团队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测试了人们将互联网整合进主观的“自我感觉”的程度。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想要再一次确认人们遇到细节性问题时,向搜索引擎寻求帮助的倾向。在实验开始前,我们编制了一个量表,它可以测量人们对自己记忆能力的评价。在量表测试中选择“我很聪明”或者“我记性很好”,可以代表一个人有着健康的“认知自尊”(cognitive self-esteem)。
我们将参与者分为两组,请他们回答一系列的细节性问题。我们允许其中一组使用谷歌,而另一组必须自食其力。当他们回答完问题后,我们用量表对他们进行测试。
使用互联网搜索答案的一组,明显表现出了更强的认知自尊。令人惊讶的是,即使他们的回答完全来自网络,人们也会错觉地认为,给出答案的是自己的头脑,而非谷歌。
为了确保这些人所拥有的“智力优越感”,并不只因为他们在谷歌的帮助下答对了更多题目,我们随后进行了一个相似的实验。我们向那些没有使用搜索引擎的人,给出了错误的反馈,让他们误信自己差不多答对了所有问题。当两组参与者自以为答对了相同数量的题目时,那些使用了互联网的参与者,依然觉得自己更聪明。
这些结果暗示,我们被谷歌拉高的认知自尊,并不只源于“回答正确”所立刻带来的积极反馈。搜索这一行为本身,使人们将 “谷歌”看做了他们“认知工具箱”的一分子。一次搜索的结果,并不同于从网页上获取的一个日期或名字,而是受试者自身记忆产生的一个“成果”。他们完全将谷歌算法的产物,当做了自己“知道”的东西。
将记忆分摊给谷歌和我们的大脑灰质,会产生一个具有持久讽刺意味的心理学效应。所谓“信息时代”的出现似乎造就了一代人,他们自认比以往的任何人都懂得多;但事实上,对谷歌的依赖,恰恰说明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少之又少。
然而,在我们成为“互联脑”(inter-mind)一员的同时,也会发展出一种不再依赖我们大脑中本地记忆的新型智力。当我们从记忆日常事实的需求中解放,就可以利用空余出来的这部分脑力资源,去实现个人的雄心。这种进化之中的“互联脑”,或许可以将人类个体的创造力与互联网上丰沛的知识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有能力突破一些自己制造的困境。
当计算机技术和数据传输的发展模糊了人脑与机器间的界限,我们或许可以超越一些由认知能力不足造成的思维和记忆短板。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陷入失去自我的危机,相反,我们不仅与其他人类拍档建立了交互记忆系统的合作关系,更与互联网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资源建立起联系——我们只是将自我融入了一个更伟大的事物之中。
本文译者 邹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应用心理专业,研究方向为积极心理学,现为交互设计师。
请 登录 发表评论